時間:2014七月
地點:菜園村周思中的田地上
受訪者: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教授)
訪問者:黃孫權,周思中
訪談整理校對:魏珊
周思中:我來先問一下關於你自己專業的問題,為甚麼搞文化研究,然後去搞教育?
許寶強:沒有問題,先問一個簡單一點的,比如說問年紀多大。
黃孫權:恩,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許寶強:許寶強。
周思中:多介紹一點可以不?
許寶強:我本來是搞文化研究的,後來搞教育。你現在可以問,我現在答就比較容易。
周思中:對,那你可以談一下為甚麼有這個轉變?或者其實是不是一個轉變?
許寶強:當然不是,文化研究就是教育,所有東西也是教育,我從小就喜歡教育,小的時候就想當一個好教師,真的,沒騙你,雖然那個時候沒有碰見黃孫權老師作為榜樣,但是我也碰見很好的類似他的老師。我想教育是我一直都關注的,沒有離開過。
黃孫權:所以文化研究才是一個旁支?
許寶強:文化研究就是教育,你知道文化研究的緣起嗎?本來是教育,是從成人教育計劃裡面出來的,起碼在英國文化研究本是成人教育,所以不是轉變。我那個時候進文化研究是很偶然的,不是計劃的。我念的是政治經濟學,本是數學家,然後鑽研政治經濟學。偶然的機會嶺南大學翻譯系要請一個老師,那個時候沒有別的人,要請我,沒辦法,我就去翻譯系。翻譯系裡面莫名其妙要教一些社會科學的翻譯,進去以後,又搞了一些翻譯理論等等,比較正統的那些文學翻譯搞不下來,後來轉到通識教育學院,陳清僑那個時候過來,又搞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通識教育學院裡面的一個項目,那個時候他說你們可以選擇留在通識教育學院。通識教育學院未來要發展兩個主修項目,一個是哲學,一個是文化研究。我肯定不是哲學家,一看就知道,所以我就——
周思中:因為你要改造世界,你不是要解釋世界。
許寶強:沒有,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哲學家。
周思中:你怎麼看,文化研究出了很多學生投入社會運動。
許寶強:提供一些資源,我覺得推力不在於學科本身的轉化力量,而在於整個社會的推動。當然,是在這個大潮流推一把的那個角色。
周思中:跟老師的榜樣有沒有關係?
許寶強:這個你回答吧。
周思中:太久了。
許寶強:我們常常從外面請一些很好的老師像黃孫權,你受他的影響,他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很有感染力。像這些老師就影響我們的一些學生出去,大概是這樣,你本身是一個。
周思中:你這幾年開始去種田,跟你思考教育、文化研究和整個社會的大形勢這方面的問題之間有沒有互相幫助?
許寶強:我是很認真回答你這個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關係。我跑去種田,我想跟你們開始的目的不太一樣,我沒有一個很大的社會計畫,是很個人的。你走到生命的一些點,我比你大大概二十…
周思中:剛好二十。
許寶強:二十歲,對,我是五十四,現在他(周思中)是三十四。我是五十歲的時候開始下田,到五十歲的時候,我在嶺南大學呆了二十年,是我唯一一個全職教書的地方,以前在別的大學兼職。我現在也跟學生提,覺得一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工作崗位太長時間,我講的“工作崗位”不是你的志業,你可以在農上面將一生放在裡面。二十年我覺得可以考慮轉一轉不一樣的工作場域。我是這個心態,覺得應該要轉一轉,雖然搬了一兩次辦公室,但是還是那種辦公室的狀態,二十年以後整個身體狀態變了,有一些毛病出來,比如說腰、背、眼睛等等,精神狀態也開始走下坡。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轉變,種田就是受你們影響。
周思中:可以健身。
許寶強:對啊,你(周思中)真的很漂亮嘛,你看,你真的這麼漂亮。
周思中:火星,可以去火星。
許寶強:你是最漂亮的,你知道嗎?
周思中:謝謝,繼續。
許寶強:當然那個時候也有不少人在看半農那些反思性的東西,我覺得試試看也好,反正我沒有比較長時段的身體勞動的經驗。平常我工作以外,保持身體主要是爬山,大概是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一次,但是種田還是不一樣的,所以就試試看。四年前在家附近租了一個田種下去,中間很多東西開始發生轉變,包括身體上的。比如說吃東西的時間,現在早上會吃多一點,下田以前吃多一點;身體更容易出汗,我們叫“清汗”。之前坐了二十年的辦公室,一身毛病,有腸胃的毛病,也有慣性的咽喉炎,大概十幾年了,可能跟教書有關,常常也看中醫調理身體,其中一種解決方法就是多一點運動,清汗就可以排了。那時候就嘗試進健身房,其實不行的,因為健身房有冷氣,那時候發覺出清汗是很難的。現在去田裡不到半小時就全身出汗,像這一類身體上的改變是很明顯的。身體改變對精神上的改變也很顯然,下了田以後感覺疲勞狀態的頻率是減低了,以前坐在辦公室一整天,回到家身體整個非常疲勞,現在反過來,早上去了一兩個小時的田,下午再去一趟,晚上的精神疲勞感減輕很多,這是身體的改變。在思考上、教育工作上,發現有一些以前念的哲學,以前不是那麼懂或者讀的時候以為懂了,像念海德格爾。他講思考是甚麼——今天我們搞通識教育,老師講批判思考,每一個人講批判思考,但是我覺得更根本的批判思考的前提是思考,因為批判被講得離題了,很多批判就是罵人,或者是你講正的我講反的,那樣是形式主義,還沒有到思考的層面。那麼思考是甚麼?怎麼思考?——看了海德格爾,他有《What Is Thinking》,一本小小的書,是一個演講稿。以前看的時候以為自己懂了,他說thinking很簡單,就是 ”be open to things approaching you” ,那個東西向你展示,放到你面前,你打開你自己,這個來的東西,它invite me,你response,回應它,這就是thinking。好像懂一點,教通識課的時候也講這一套。講來講去,再講具體例子也很難講。那時下了田,就開始用田的一些感覺來理解。比如說現在立秋要播種,種子來了,你怎麼去回應那個種子?種子發苗了,那你怎麼回應這個苗?甚麼時候下?苗長出來,被颳倒,你怎麼處理?買這些亂七八糟的是哪一類的比較好?粗一點還是幼一點的?所以那個東西,也跟Richard Sennett關聯,我的興趣,也是從這裡來。這也跟一些教育理論相關, Michael Polanyi 講的 Tacit Knowledge (戰術知識),就是甚麼叫學習,甚麼叫知識——他說所有的知識就是personal的知識。甚麼叫個人的知識?你要經歷過你處理對象的過程,然後才有所謂的知識,不然人家告訴你怎麼種田,甚麼東西要早一點下等等,聽完以後好像知道了,但是你沒有做一遍或者走過一個過程;比如說周思中教我像發苗兩三天米大概會出一些白的點,出白點的時候你要弄甚麼,你聽當然會明白“恩,我知道那個”,但是你不弄一遍的話,大概永遠無法深刻地知道,也無法再講給其他人聽,即便講給別人聽你自己也不曉得自己講甚麼。就像我以前念法蘭克福學派,其實我不曉得在講甚麼,只可以念出它幾句話,我覺得這是他講的個人的,是一種工藝、 Tacit Knowledge,你不能完全講得出來但是你得身體經驗。所有的學習就是這樣,所以教育可能最根本是跟農業這種操作更相關,到農藝裡面的那個過程。就用農藝吧,農藝比較準確一點,如果從教育角度去講。這回答你怎麼跟教育有關,合格嗎?(大家鼓掌)。太好了。
黃孫權:香港這十年來的社會運動跟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有關,就好像台灣早期的社會運動會跟台大城鄉所有關係一樣,你可不可以談一下,這十年來你們怎麼想象學院的體制?你們很多優秀的學生搞媒體、搞運動,最後變農夫,你怎麼想象這個體制?
許寶強:我覺得可能是一種聚合,有點像階級的那種觀念,不是設計出來的。在三四年前,嶺南大學crossroad十週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調查研究,訪問我們過去這七八年畢業的學生,問他們在嶺南大學念的那些怎麼樣,做一個檢討。大部分跟我講你們教的傅柯啦、法蘭克福學派啦全忘了,就是一開始就沒有讀進去,從來不曉得你在將甚麼。但是覺得你們老師這個群體還是有心,聰頭(葉蔭聰)搞InMedia,這個常常跑山區,那個去中國大陸,像陳順馨、劉健芝,那個時候搞公民黨,還有副校長他們每一個人手頭上大概都有一些東西在做。在報紙上寫的文章也好、平常的操作也好學生都看得見,主要是是這樣,而不是設計的體制。我們很用心地設定文化研究的課程和教學法反而不是很相關,它不會引起學生關注社會。這不是謙虛,我覺得是大社會的環境推動,學生可以看見一些老師、高年級的學生參加了社會活動。我們前期收學生也很有意識地選一些在社會里搞活動、有經驗的人,比例不多。到後來大概是2003年,我們辦 MCS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那個有一點不一樣,我們有意把在各個環節裡面的專業、不同領域的朋友拉過來,他們願意有一些 intellectual back-up(智囊),就是知性上的那個。今天你在社會運動圈裡面常常看到的比較主要的那些組織者,幾個已經很夠了,因為一般幾十個人裡面大概有五六個很活躍的,他有一些社會網絡,跟其他同學(一起),其他同學在社會有不同的經驗,有些做出版,有一些做媒體,也有一些社會工作者等等,不同的領域。領域間的互動在某個程度上打造了這種氛圍,更多是學生背景的網絡。我們有不少這些學生,每一屆大概十個左右,有一些是參與很積極的,有一些不是那麼積極,但是也會參加。過個兩三年大概就有一個網絡,十幾個人,我們就搞一些financial tsunami(金融風暴)那些非正式的討論,出一些書,他們自己也另外搞一些獨立的網絡活動。部分可能也是在 MCS 裡面放生的,你們碰見,然後產生一些互動。
所以我想大概是這樣,跟課程內容設計關係不大。我現在反思自己講文化研究教育真的可以講幾個小時,但是我不會講那個,這種源自英美的我們叫 critical scholarship(批判學者),轉移到香港這個脈絡下來操作是有很大局限的。引進這些批判性理論,是有一些前提的,但是我們香港的脈絡,特別是我們大學生的課程教具,本科生的生命經歷跟他們學理的配比,不是英美出產的 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論)那種脈絡。你們台灣的文化研究,陳光興那一代弄的時候還是比較精英的。現在文化研究比較普及,差不多所有學校多多少少搞一點,但是很多學生的背景不是那種可以看書就沒有問題,沒有的。怎麼處理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好好反思重新再弄。
剛才談到怎麼重新去思考教育跟搞農藝的關係,我覺得反而可能更有效果。最近十週年,MCS請了幾個人回來談“身體、情感與記憶的教育”,“body, affect, technique”跟過去那個你簡單講知性上的,是很不一樣,包括內容、教學法也完全有思考,所以我說不是decide的問題。
黃孫權:但是這樣講也很矛盾,因為如果教育課程的安排不重要?
許寶強:不在那個層次發生,但是教育是發生了。在嶺南大學,在文化研究系那個氛圍、脈絡裡面,有一些東西是發生了,學生跟學生的互動也產生了很多教育的效果。他們到外面去參與農藝的一些觀察,或者是去菜園村,去不同的社區里搞互動,確實是發生了很多教育的效果。而我們的課程設計,有時候可以連結一小部分,但絕大部分我覺得連結做得不好,我們沒辦法把這些來自英美的很好的批判理論做到跟學生的日常生活扣連得比較好。我覺得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周思中:但是我覺得老師的榜樣還是很重要的,你新進到一個系,看見老師做東做西,自己會很有體會。
許寶強:那個正規的課程扣得不緊,當然你有時候在報紙發一些文章,可能學生讀起來比你在課堂上面的演講更直接一點,因為你談的可能是他們平時也關注的時事,不同的對話在那裡發生。但是正規課程我覺得還有很多空間,很多東西可以做,這個我說可以講幾個小時(既然教一門課),我講下去擔心你們真的會設備沒有電。你若有時間,我們12月會搞一個teaching camp,我會做一些報告。簡單講就是一些課程內容可以很好地結合,但是要從學生的生活出發。我今年教一門課叫研究方法,那是去了你們高雄以後慢慢發展出來的反思。以前教研究方法,研究對學生來講是最苦悶的。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的計劃,要教他們各種學術研究的技巧,或者是反思性的一些理論,methodology(研究法)。只有一小部分學生對那些東西有慾望、想繼續做這一類,大部分(我問過以前那些畢業生)覺得最苦悶的一門課就是方法。
周思中:那一般都是introduction的,一開始就要念?
許寶強:要念,必修的一門課。但他們覺得沒甚麼意思,他們覺得我畢業以後做的工作要才不需要學術研究,開玩笑,你搞甚麼,誰要你語意學分析,誰要你做甚麼訪問的技巧,甚麼focus group(焦點團體訪談),你搞甚麼搞,我現在要去幫人影印、復印……一個學生是這樣跟我講的。有不少學生——特別是不走學術道路的——覺得學這些東西很痛苦,也要不斷地去圖書館找一些bibliography(參考書目),我覺得是有問題的。當然我們那個時候覺得非常重要——你不學好這個你怎麼理解那個?因為我們有一個假定,二十年前我們念大學的時候,大概只有百分之幾的學生念大學,很多這些大概是很有條件或者是也準備去外面念書的,當然無所謂,你幫他們準備。像英美那些文化研究,很多是大學生的程度,你已經是研究生了,當然這些東西就直接幫你解決問題。但是它不能幫大學生解決問題。所以我今年還是教研究方法,我們想告訴他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同時真的是研究生,我是很serious的,做事情若不研究,其實不是做事情,而是應付一些東西。那個物到了你前面,你不思考的話,就不曉得怎麼弄。所以最好的工匠本身是一個很好的研究人,他把每一個東西都看得仔細,農夫是一個非常好的研究者,不是好的研究者做不來好的農夫。我大概是這樣跟他們講,當然,他們不明白我講甚麼,那無所謂。
周思中:可能批判理論更難明白。
許寶強:那我怎麼做,我說,那好,簡單一點,做研究是甚麼,就是解決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有甚麼問題來解決?然後讓每一個人講一些要解決的問題。其實這個步驟也非常困難,因為經過十二年的中學教育,大部分學生大概也沒有問題,而且他們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老師要我解決甚麼問題,那我就解決甚麼問題。十二年教育的信念就是叫學生應付高考、應付考試對你的要求,你整個生命大概是應付那個,所以讀書全是應付的。這種身體習慣,十二年以後,你問他“你有甚麼要自我解決嗎”,很多學生才開始發展這方面的思考。結果整整一年時間,只跟他們一起做一個事情,就是找一個題目,整年時間只做這個。我教的這門課是一年method1(研究方法一)、method 2(研究方法二),我特意要求要教一年,因為半年沒可能。
他們提出來題目,我們討論,我也不反對他——有個學生愛足球,想做香港政府的足球研究,你看解決這個問題要做甚麼事情。我幫他分析,你大概要在政府的網站找找政府的文件,看看他們資源怎麼分配,找一些統計數字等等,然後訪問一些人。他做了一小點那些,他說挺悶的,就反思我真的是想做這個嗎?他做了一兩個月,覺得還是變得比較難。
有些學生進行得比較快,他大概沒受那十二年(教育的影響),大概不是那麼好的學生,對這個遊戲玩得不是很熱心。有一個提得非常好,一早提出來:我為甚麼整天無無聊聊、渾渾噩噩,特別是在長假期裡面。我說非常好,我們就討論這個,討論怎麼好。其實我的作用很簡單,所有學生提的題目我都說很好,你們就做。他們講不出怎麼好,我就幫他們想一個方法講是怎麼好,他們聽到不同的好處。像政府足球那個我說也挺好,很有意義,題目很清楚,要找甚麼很明顯,所以非常容易做等等,去做就好了。他真的去做,碰起來就不感興趣。
研究無聊這個好,我說這是非常貼心的一種感覺,所以這個可以last for a long time(維持一陣時間),你不會離開它的,不是解決他人的問題,而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他沒有信心,擔心這個會不會太個人、太自我,沒有社會關懷,因為文化研究好像要有社會關懷。我說這個很有社會關懷啊,你跟同學討論,看看誰有這個經驗。結果一開那個tutorial(習題討論),多半同學也說長假期一樣無無聊聊,真的很無聊,上Facebook半天也不解悶,不好玩,有差不多半個班以上同學有共同的感覺。我說你看你多有社會意義。那個同學感興趣香港政府的足球政策的發展,誰也感興趣?很少。他的社會意義不是很多,但是個人關懷,只要稍微倒轉,會不一樣。
有一些同學聽了這個,就覺得也可以往一些以前所謂很個人的工作裡面去做。後來這個做足球的同學做了一個學期發現不夠,他說我可不可以稍微改那個題目?我問怎麼改,他說去參加足球的青訓班,覺得青訓班不爽,因為那些人不公平,他講了很多小故事。我說挺好,你就做你為甚麼在青訓班不爽,他就這樣搞下去。一年之後他交的題目就是“我為甚麼在青訓班不爽”,討論是不是可以讓大家爽一點。
那一屆的題目有很多,有學生從去超級市場買東西開始,這個題目做得很感動。她兄弟姐妹四五個,她是最小的妹妹,負責家裡面要買日用品,就是routine shopping(購買日常品),很困難。你知道香港現在shopping主要是幾個超級市場,他們是低收入階層,要講價,要比較那些價格。開始的時候我以為她的題目是“哪一個地方可以找到最便宜的商品”,我說好啊,你就去做。她就去比較這幾個部分。後來發現我買或者不買不是僅僅考慮價錢,另外還有一些東西,比如遠不遠,我那天要買的東西是不是降價——她買那個廁紙,一大排那些,減價的時候。當然如果離她家比較遠的話,就比較困難。所以她要考慮很多這些條件,要配合時間等等很多東西,不僅僅是價錢問題。那麼我關心甚麼?我就是不斷地問同一個問題——你要解決甚麼問題,for whom?for what?整年就是問這兩個問題,反反復復用不同的方法提問。她順著去想,後來越來越打開,考慮我為甚麼要買這個,原來她是維持她的家庭,她覺得這個家庭裡面她要幫忙做這個事情,家裡面有一些東西可以照顧。她同時要讀那些shopping theory(購物理論),consumerism story(消費理論),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那些理論,她以前搞不清楚那些東西是甚麼。但是她搞了一段時間這項研究,她說我現在看懂那些理論,她最後literature review(文獻回顧)寫得非常好。她說,有一些批判shopping、consumerism那些是不對的,不是這樣,現在消費者有很多消費方式,不一樣,像我這種消費是有點 Danny Mueller 那種,我也建議她讀那個。她後來就讀出來了,她說這些法蘭克福學派說我們很笨,不是的,中間她體現所謂理性shopping,routine shopping很多。之前大概是看不懂的,但她願意去讀,我告訴她說這個是解決你的問題的,她半信半疑地去看,經過一年的討論,從旁邊各種鼓勵她,就發生了一些轉變。我現在的作法就是讓他們覺得研究真的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這種研究我們稱為action research(行動研究),其實是學理一點的,可以解決問題的。但過去我們的教學不是這樣子,大概是經過十多年的反思,以前做錯很多,就像下田,我犯了很多錯誤,不斷地犯錯誤。
周思中:所以理論還是重要的,像你說的那樣。
許寶強:對,所以curriculum(課程)我們要改變,他還是有用的。我反過來就是說articulation(連結)可以做得更好,以前我們搞文化研究對教與學那個部分重視得不夠,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場域反而還是教育,而不是前面的popular culture(大眾文化)也好,film study(電影研究)的那個文化研究,那有專家在做。他(周思中)最近出了一本書,你們杭州美院來的,不能不理解這本書,一定要知道。
黃孫權:你有周思中這樣的學生是不是覺得很驕傲?
許寶強:他是我的老師,你知道我下田是怎麼捱過來的?我沒辦法進行下去,那些物進來當然你可以思考,但是腦筋轉不過來,你要有那個經驗,學習方法不一樣。所以我手機不離身,一有問題就打電話問,前兩天你不是收了我一個電話嗎,你坦白從寬。
周思中:有一個電話。
許寶強:對,我在米田裡面,米現在出來了怎麼辦,收水是甚麼時候。他去年講過一遍,但是我忘了,不是很有把握怎麼看那個情況,他說灌漿以後,稍微掉下來大概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收了,我知道還沒有到時候,就弄別的一些東西,所以他是我的老師。他不僅僅是學生,同時也是我們的老師,我不是講那些理論上的話。我們的物、教育的物是甚麼?就是學生,你是教育工作者,他們來到你前面,用那個海德格爾那種講法,你怎麼回應?你首先要理解你學習那個木頭是怎麼樣的,所有的東西也是我們的老師,你不跟他學,讓他跟你學是沒道理的,沒可能的,對不對?這是認真的。
黃孫權:好。請就你的觀察,談一下這十年來香港的社會運動跟媒體。
許寶強:你覺得剛才我講的這些是不是一種社會運動?我其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社會運動,當然有它的領域,但是如果我思考這個問題,會想這算不算社會運動,或者社會運動應該包含甚麼東西在裡面。像他(周思中)來種田,你剛剛說他甚麼?
黃孫權:淡出,歸隱。
許寶強:是淡出還是深入社會運動,這很難說。因為從某個層面,我覺得他可以重新打開社會運動。當然社會運動有我們很習慣的一種形象,比如說“七一遊行”,那是很直觀的,是社會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個部分。那麼這個部分的發生,離不開其他的條件、前提,進行了這麼多,它也有歷史,它是怎麼走過來,這些人是怎麼發生轉變的等等,有當下的一些他們經常講的大事件,一種轉換。但是同時在這個轉化過程裡面,也還有很多不同的歷史經驗,在不同領域,我不太懂。但是我比較有把握談或者是想談的還是教育,你覺得教育跟社會運動有關係,我可以多談一談,沒有的話我覺得——
黃孫權:當然有關係,請談一下。
許寶強:就剛才講那一種轉化——
黃孫權:在整個香港的大專、大學教育裡面,你們嶺南大學是非常獨特的,其他的大學教育或研究所不是這樣操作的。
許寶強:也不能這麼說,因為我沒仔細看。當然不是普遍,在嶺南大學內部也不普遍,嶺南大學裡面的操作,我覺得還是沒有一種公益的理解在裡面,也不是個人知識那種傳統,還是一種banking system,(銀行系統)從下到上的一種設計。簡單講就是我們覺得有一些知識、技能是很重要的,我們相信有一些方法可以把這些技能教給學生,香港絕大部分就是這樣安排下去。如果你不是這樣做,那對社會運動主體的生成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效果?如果有,那兩者的關係就結合起來;如果沒有,像剛才講那些一年級的學生,他們剛進來,四年裡面二年級才是我們一年的主修,第一年沒有主修,他們跟香港的絕大部分大學生一樣,不會跑到菜園村的前沿,也不會在七一那天的最前面,他不會的,甚至可能有點抗拒,懷疑是不是要這樣弄。這些學生,他們面對我們想象中的這種社會運動,當然不是認為很激進、沒有道理或者是搞破壞,他們不是這樣理解,但是社會運動要跟這一些比較大範圍的青年或是所謂不那麼激進的人有對話的話,前提是甚麼?我覺得前提可能是有一些很根本性的東西,如果說他們沒有問題,沒有提問的能力與習慣的話,那很難結合的,我自己感覺那樣主體性是很難召喚出來的。所以我覺得你跟他們講馬克思說要改變世界,或是你講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或是分析說現在你不出來香港會滅亡等等,我覺得你交流這個知識,也是banking system,就是沒有結合他日常生活過去十幾年的歷史、身體習慣。那拐一個彎,如果他習慣你教導一些他感興趣的問題——我明白我參加足球青訓營要爽一點,現在不那麼爽,不爽是甚麼原因?你一追這個問題,大概就會支持反東北發展計劃。我有信心,你要這樣追下去,為甚麼青訓營不爽,土地你用來打高爾夫球就沒有足球場,或者越來越小。若沒有這個提問,你讓他結合他關注的那些,我覺得有困難。所以這個我不曉得是不是社會運動,可能…
黃孫權:是,很厲害。可是我的意思是——我還是照一般社會學的觀點來說,我們還是結構性地討論這個事,譬如我覺得我跟思中是不同代,“七一”那天有更年輕的一代進來,比起前十年,社會參與越來越熱烈。你怎麼看待這十年?這是一個偶然的聚合結構嗎?還是背後有你說的那個大的推動力?
許寶強:有,當然有,若分析這個結構性轉變,很多人談過,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像上次去台灣那篇文章講新自由主義那種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平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統治階層用的暴力方法越來越容易暴露,青年的出路,對比以前十多二十年前出路相對比較窄等等,各種結構的一些因素。在大學生裡面,過去比較單一價值觀下的那種path不那麼容易走下去,越來越多我們以前叫作不那麼好的學生,他不會成為律師之類的。那反而有一種可能性——反正我也做不了那一種,那東西就開放出來。有機會反而是一個最大的困難,主體生存的困難。我現在看一些關於情感的討論,說我們的恐懼或者是我們的inactive(不能動)的那種狀態,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希望,完全沒有希望的人倒無所謂,而是我們還有希望,覺得還是有機會,如果我好好地念書,還是有機會當一些教授、美院的藝術家等等。當還有這個希望的時候,其實是更困難,你還是比較擔憂,比較inactive,那個理論這樣講我覺得有一點道理。反而是沒有這一種空間,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這條路不好走下去,那反而有一些開放性。如果這樣做的話,我覺得那個前提要出來,就是還是要提供一些,我們講,提供一些講法,這一種好像是被逼的東西變成主動性強一點。
所謂的 Civil Disobedience,公民抗命,開始的時候談比較集中在公民素質的討論,一個公民應該怎麼樣,要理性、非暴力等等。抗命運,抗命定的一種過程,這種抗命其實是一種生存的態度,是一種生存的習慣。
所謂的 Civil Disobedience,公民抗命,開始的時候談比較集中在公民素質的討論,一個公民應該怎麼樣,要理性、非暴力等等,有關抗命談得不太多,我就寫了一篇文章稍微談了談,談得不是很多。抗命是甚麼意思?抗命運,抗命定的一種過程,這種抗命其實是一種生存的態度,是一種生存的習慣。有一些東西會這樣走下去,但你感覺不那麼好,剛才那個同學,要踢足球踢得爽的話,現在這麼走下去不會爽的。那你想爽還是不爽,踢足球的時候,你如果還想爽的話,你就要把阻擋你爽的一些東西踢開或是不要理會,抗命大概是這樣的。我最近看他們的學生,受老師影響非常大的那些演藝學院的學生,我很佩服,他們做了,他們的那種反彈我覺得非常好,就是不爽,就是抗命,林鄭月娥過來,就是去發表了甚麼拿史丹福榮譽那個人,不是你個人,不是因為你林鄭月娥一個很厲害的人,而是你代表政府,所以你站在那個位置,但你是讓我們不爽的源頭,我為甚麼還要尊重你?這就體現那種抗命。想想看,如果整個香港越來越多這樣的學生,在各個領域讓這些人每出來一次,本來佔這些位置的人就要想擁有一種榮譽,但那每一次發聲讓你難受的就是你的成本,你做這些壞事情的成本,這就是公民抗命。所有的每一次都是這樣,你買菜,我就不賣給你,我好的菜不賣給你,你不應該吃好的菜,因為你破壞菜田,你吃壞的菜,等等。每一個領域都是像這樣,你想想看,這就是社會轉變。當然是很困難的,我在想怎麼引入這些,教育工作就是讓多一些像他們的學生出來。
黃孫權:這個有意思,很不錯。但大學本科生,他們大部分都會看Facebook,對不對?不會看InMedia?還有instagram,你怎麼看待這些很快捷、很大的商業媒體、社交媒體?
許寶強:我個人有點排拒的,所以我不玩,在上面只有幾個朋友,他(周思中)知道的,全世界只有八個朋友。
黃孫權:你的學生都看。
許寶強:我知道,我其實也有掙扎,就是參加不參加進去,因為很多東西我脫離了,我知道的,所以我要找另外一些人,這八個朋友是我很重要的。
黃孫權:維持你跟外界的關係。
許寶強:這個問題我這樣理解,可能不是回答你關注的,但是我這樣理解,你看他們可能更少看InMedia,也反映這些alternative media本身的一些局限,我剛才講大部分學生不會很主動地看,雖然看InMedia的越來越多了,但是所謂越來越多,那個比例還是不大。我相信主流派講不錯的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比例,但是不像他們講的這麼絕對,有變化。那怎麼處理這個差距,他反映出那個gap本身還是挺大的,Facebook的關心者或者是熱愛者,我們如果想跟他們對話或者是想讓他們也變成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們過來,一些玩Facebook的人在你面前,你怎麼回應,我想是這樣子。我想InMedia的朋友大概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能夠看到那個gap還是比較大的,雖然看的人越來越多,但還是有一個鴻溝。當然也有體制上的不利的因素,比如說回家打開電視,不過可能不對,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身體,你們不一樣,所以主流媒體的影響對我們還是比較大的。Facebook我真的不太理解,我想講就是那個鴻溝可以觀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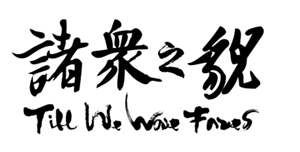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