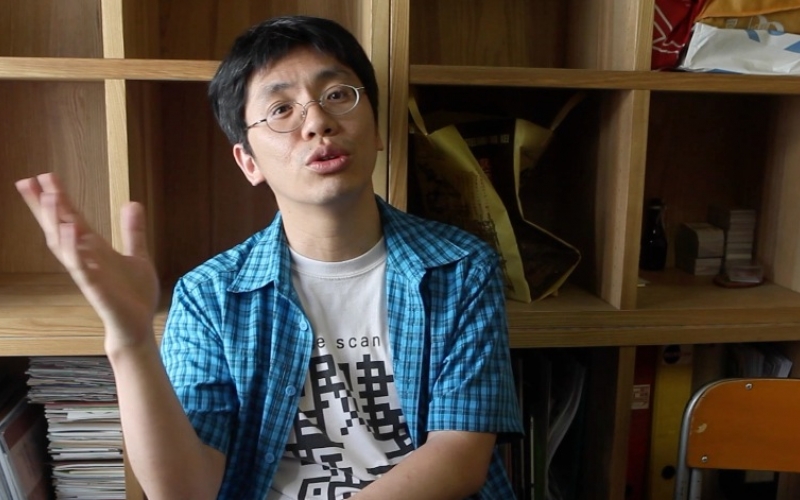時間:2014年7月2日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辦公室
受訪者:葉蔭聰(獨立媒體創辦人,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現任教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編有《没有小贩的都市?》《迪士尼不是乐园》《穷人系懒人?》)
訪問者:黃孫權
採訪整理:魏珊
黃孫權:能否先講講你跟藹雲(林藹雲)創立「獨立媒體」之前的經驗?
葉蔭聰:我們都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在讀書的時候加入一些學生社團。參與學生報和一些社團的小型刊物。畢業之後,在不少小報刊、小雜誌裡面工作,通常都是非牟利的,跟社會運動、民間團體有關。整個90年代我們前前後後做過四五個這樣的小刊物,讀者可能不過千人。最後一個是我們1999—2000年的時候做的《街角》雜誌,是一本像書一樣的雜誌。「獨立媒體」是2004年創辦的。一開始想的比較簡單,by issue,一期一期的出,直接把我們90年代辦刊物的做法放在互聯網上,後來發現互聯網好像不是這個樣子,於是就開始做調整。互聯網影響了很多我們之前的運作模式,大概是這樣走過來的。
黃孫權:2004年具有甚麼樣的機會或者契機讓你們想要做「獨立媒體」?
葉蔭聰:2003年的「七一遊行」官方統計超過50萬人,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國家安全法》23條,這個遊行有非常大的震撼力,特別是對當時的特區政府和臨時政府。於是很多政府裡的人覺得這麼多人上街是有特別原因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媒體。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2003年的前後,一個非常重要的媒體就是電台,當然報刊就是《蘋果日報》之類。
黃孫權:講講當時的電台。
葉蔭聰:2003年的「七一遊行」,上街的人數超出政府的預期,政府的人當然會研究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去上街,他們其中一個結論就是媒體,特別是當時的電台。香港當時非常流行台灣的「call-in」節目,我們叫「phong-in」節目,市民打電話給主持人,通常主持人的立場非常鮮明,他們對那年的「七一遊行」是有動員作用的。估計因為原因,2003遊行之後的一年裡面,很多的電台的主持人,都相繼被迫離開,更有傳聞說他們受到了暴力恐嚇。我們當然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很多本來非常政治化的、有社會動員能力的電台節目的主持人都離開了,這就讓很多香港人擔心香港媒體的自主受到了威脅,這就激發了一部分人自己出來辦媒體。我們都知道那些大的媒體背後都有老闆、財團,他們跟政府的關係非常好,自己辦媒體就是認為指望他們是不行的。創辦「獨立媒體」討論和籌備是在2004年「七一遊行」之前,遊行之後我們成立於下半年。再往前推,在2003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小規模但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網上媒體,2003年遊行之後,互聯網就更加熱鬧了。有一個叫「香港人民廣播電視台」的網上電台,是當時收聽人數最多的電台,比我們早大半年的。我們出現的時候,身邊還有很多網台、網站,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到現在,那些透過互聯網成立的民間媒體,幾乎只剩下我們了。
黃孫權:從2004年開始到現在,運作上有甚麼轉變嗎?
葉蔭聰:當然有很多很複雜的轉變,簡單說就是我們在2009、2010年之前比較像是一個社運媒體(activist media),媒體行動主義。這本身也不是我們詳細計劃好的,我們這些人都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部分還是組織者,所以很自然地,做法跟其他的新聞媒體很不一樣。在媒體裡面呆過較長時間的人,只有林藹雲,媒體的信譽值受到籌辦者的身份影響,我們這些人都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部分還是組織者,所以很自然地,做法跟其他的新聞媒體很不一樣。我們是甚麼人,那個媒體就是什麼樣的。例如有時候我們的成員參與到某些社會運動,就會讓整個媒體的內容跟運動有關,其他的內容就很少。最明顯的是2005年反世貿,2006、2007年天星和皇后碼頭運動,在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我們經歷過一種不自覺的媒體行動主義的模式運作之後,發現很多問題,覺得沒辦法用這種方式運作下去,我們內部也開始討論接下來要怎麼去做。第一,假如我們是一個所謂的社會運動媒體的話,我們好多人跳來跳去,這樣子不好,真的要搞運動的話,就在某個領域搞下去,應該重新定位。第二,我們是2006年左右進駐這棟大樓的(富德樓),有一個辦公室,這個地方現在看起來很亂,天星、皇后碼頭運動時候更亂,都沒辦法進門,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黃孫權:那時候很像一個運動中心..
葉蔭聰:對,任何跟這個運動有關的人都會進來。只要是運動在進行,都是亂七八糟,很多事情沒法運作,我們甚至沒辦法開會,所以要重新調整。到了2009年我們的自我意識比較清晰了,認為我們跟社會運動團體應該有所區別,媒體的功能應要加強。另外有一個原因也跟這個轉型有關。我們一開始鼓勵citizen reporter(公民記者),每個人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去作一個citizen reporter,就像美國的blog journalist(博客記者),那時候台灣就有不少以個人的身份去做citizen reporter的非專業記者,網站只是一個平台。但是從2004年一直到2008、2009年我們發現這種人在香港很少,儘管我們很大力地去推動,搞各種各樣的活動去鼓勵。我們曾經花很大力氣培訓公民記者,辦了很多工作坊,但到了2007、2008年已經感覺到香港相對其他地方來說可能更沒有土壤出現個人身份的公民記者。我們獨立媒體要做公民報道,若我們不再是一個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的社運團體的話,就需要有人做記者,要生產內容,我們要有自己的公民記者團隊。
在2009年之前,我們只有一個很鬆散的網絡,有些人因為是社運的參與者,他們就自稱是我們的民間記者,但是我們其實沒有固定的關係。2009年之後我們就開始有自己的團隊,有比較清晰的登記制度——誰誰是我們的記者,我們也發名片、記者證給他,讓他進入一些可以採訪的地點,包括立法會等其他的官方機構。我們也配合實習的計劃,很多學校有學生過來實習,我們把實習記者也招進來變成我們的記者,我們還弄了一些名堂給他們,叫他們為特約記者,其實我們也不懂甚麼意思,反正是個身份。這樣我們就開始有了自己的團隊,成員來來去去,有小部分的人是比較固定。這個團隊從2009年到現在規模基本維持或有一點點增長。
黃孫權:你們現在有幾個正式的staff?
葉蔭聰:這段時間比較特殊,有一位專職生小孩,我們多聘了一個替工,所以現在有四位,之前有三位,有兩位工作集中在我們的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到2011年左右,除了自己做媒體還要介入跟媒體有關的領域,我們稱之為媒體政策,於是我們多聘了一個staff主力做媒體領域方面的事情,他跟我們網站的關係沒有那麼直接,主做倡導的工作,包括版權法,資訊自由法等等。我們沒有任何一位記者是受聘的,兩位staff是採訪或者編輯的角色,由他們統籌特約記者。
黃孫權:有幾個特約記者?
葉蔭聰:這要問Damon(獨媒編輯),因為來來去去,現在有很多特約記者我都不認識。比較固定的大概有十個。
黃孫權:2009年之前你們有審稿制度嗎?
葉蔭聰:沒有。
黃孫權:2009年之後呢?
葉蔭聰:我們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是自由上載,2009—2010年之後我們有了自己的特約記者,假如是我們自己的特約記者的稿,就要經過編輯審,不是的話就可以自由上載。
黃孫權:審核有甚麼標準?
葉蔭聰:我們有一個編輯團隊,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有改,因為通常他們新聞寫作最基本的東西都做不好,我們就幫他改寫作的部分,有時候是裡面的一些事實我們要搞清楚,最主要是怎麼樣把東西組織起來。我們這裡的實習生,可能跟一般的新聞機構不一樣。一般新聞機構裡面,去實習的學生主要是新聞系的學生,受過最基本的新聞訓練,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處理,但是我們有非常多非新聞專業的實習生,他們可能搞不懂新聞的一些基本,把事情講清楚,是最簡單的一個原則。
黃孫權:你們既是平台又是媒體,這兩個角色有時候會衝突,例如有人貼了一篇反動或者是保守的文章,你們怎麼處理?
葉蔭聰:我們不處理這個事情,就讓他上去。當然我們在網站的設計上會對應這個問題。例如在我們網站右邊有一欄放最新文章之外,中間有一個又大又寬的column(網頁焦點欄目)是我們的焦點,放我們挑選的一些報道或者評論,我們過去一兩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加強這個部分內容,以前評論的文章多是我們自己寫,或是一些跟我們觀點接近的人去寫,現在我們努力去找一些所謂的專欄作家,這種做法跟「主場新聞」(House News另一個香港新聞網站,於2014年7月26日停運 http://thehousenews.com )出現有關,模模糊糊產生出一種競爭關係。我們跟他們蠻友好的,他們做得好的地方我們也學習。blog在香港曾經短時間內非常流行,但是很快就沒落了,特別是像 Facebook 出現之後,基本上已經沒有太多人去寫,寫了也沒有太多人去看。「主場新聞」出現像是重新讓 blog 浮出水面,他們Facebook運用得比較好,善於發佈和分享他們的內容,所以很多bloger(博客寫手)都很願意去他們那邊寫文章,他們也招了一幫 bloger。blog 已經不太流行,但有些人還在寫,一些人還寫得不錯,就是缺乏推廣的渠道,即便使用 Facebook,也沒法傳得那麼遠。但是「主場新聞」就很有能力把他們自己的內容傳到很遠。我們可能比不上「主場新聞」,但是我們的傳播能力比一般的blog稍微好一些。所以也在吸引不少 bloger 進來,非常多 bloger 對事情的觀點跟我們不完全一樣,也會在我們的網站上面發表,我們也會把他們的文章放在我們的焦點版塊上面,所以只要有一定的立場,能反映我們獨媒核心成員對很多議題特別是香港的一些政治議題的立場,編輯部都會推廣,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標準。我們自己也會寫editoral,每周編輯之間輪流寫。
黃孫權:請談談早期那些戰友們,他們陸陸續續去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說凱迪,周思中,小西他們。
葉蔭聰: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我剛才說的社會運動了,或是社會運動的後續發展。周思中現在去做農民,跟他參與到菜園村反高鐵有關,他曾經是我們的staff,現在比較少參與「獨立媒體」。朱凱迪現在還是我們的編輯,這些人都是來來去去的,我們還是活在一個蠻廣的社會運動網絡中,這些人不在「獨立媒體」擔任職位,但他們還是在這個網絡裡面。每一個人都有點不一樣了,有些人可能不是社運裡面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仍在廣義網絡裡。就像我們以前一個比較核心的成員Freddy,他後來搞了一家小公司拍紀錄片,內容常跟社會運動有關,所以還是在廣義的這個圈子裡面。
黃孫權:Facebook興起,有非常多另類媒體跟他合作,但 Facebook 是商業運作,你必須透過Facebook傳遞訊息,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葉蔭聰:從2008年到2011年這三四年,Facebook 在香港的註冊用戶增長得最快,每年增加100多萬使用者,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就飽和了,人口就這麼多,不可能永遠增加。但這段時間我們網站的瀏覽量也是在增長的,一部分原因跟我們的運動脫離不了關係,每次運動就有很多人關注我們的內容,我們經常是很多運動特別是早期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來源。後來很多主流媒體,包括社交媒體談這些內容,要瞭解有關運動的更多議題的相關的內容去我們網站可能比去主流媒體還要方便。就這樣沒有因為 Facebook 出現減少我們網站的瀏覽量,但是所有討論的東西都跑到 Facebook。所以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影響不是沒有人來看我們的東西,而是沒有人在我們的平台上面討論。這我們沒辦法扭轉過來,因為 Facebook 成為香港人最主要的交往平台,跟其他國家一樣。 Facebook 當然是商業性的集團力量,情況就像所有上網都需要透過一家商業公司的網絡服務,很少地方互聯網的服務是國家提供的,這個是沒辦法逃避的。當然我承認我們也會受到影響,這個影響哪些好哪些不好,要很仔細地去看。比如說,Facebook 對我們的影響,除了很多人透過他來看網站,另外一個影響就是,有一個 Facebook 的專頁 page(我們大概2011年的時候用這個page),用它上載內容很方便,傳播很直接,而且在上面比較容易找到一個粉絲的page。在其中有兩個很有趣的效果,一個跟我們生產內容有關,一個跟我們接觸的這些讀者有關。在生產內容部分,由於我們要經營這個page,就很自然地讓我們其中幾個成員組成了管理 page 的小團隊,是我們整個團隊裡面的一小部分(我也在裡面,雖然我很少直接發post),可以隨時經營這個 page,發東西出去,我們因此形成了一個比較固定的媒體運作常規。我們這種媒體經常是沒有常規的,我們曾經很努力地去建立一些常規,但我們都是志願者,不受薪,不是被聘用在這裡工作的,所以很難建立我們的常規。但是當Facebook成為每一個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時候,反而比較容易形成一個常規性的運作方式。現在最固定、最有常規性的運作,就是 Facebook 的管理,它比我們網站的管理還要固定,每一天、每個小時都在經營。這個影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也說不清楚,至少現在為止對我們來說是沒辦法避免的。它也會產生另外一些跟生產有關的東西,比如我們現在會做一些即時新聞,有點像主流媒體做的事情,這個即時新聞的格式,跟「主場新聞」有關。慢慢的,我們兩邊的格式越來越像,所以有時候一般的網民在Facebook上面都搞不清楚到底那個是「獨立媒體」發的還是「主場新聞」發的或是蘋果日報發的。這是生產部分一個很大的轉變。另外一個轉變怎麼看都是一件好事,就是接觸到的讀者面很廣。比如說最近看過我們page的有14萬人次,在14萬裡面只有40%的人是香港的,60%是香港以外的,馬來西亞、台灣、美國的一些華人。Facebook在大陸要翻牆,但仍有5%,這是很不容易。在 google analytics(Google為網站提供的數據統計服務)對比看我們的獨立媒體自己的網站,來自香港的還佔75%左右,因此Facebook讓我們能接觸到一個比較廣的華人世界。而其他像台灣、馬來西亞更明顯,也是跟事件有關,比如說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馬來西亞的選舉,好多人會透過我們的專頁去看香港的事情,也會看我們怎麼樣去談他們的事情。所以我沒法評價Facebook對我們的影響是好還是不好,有些東西不能簡單說他是好還是不好。
黃孫權:2004年獨立媒體剛成立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新媒體,現在已經跟2004年很不一樣了,你怎麼看待你們的角色?
葉蔭聰:我們第一是生產內容,現在很多新出來的媒體不再生產內容,有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說「主場新聞」他們有點接近策展(curation)這個概念,我們跟他們學到不少策展技巧。但是同時我們仍保持做採訪,也嘗試真的去挖新聞,當然他們也做,但是他們做採訪的比重要比我們小很多。相對其他一些新出現的香港媒體,像「輔仁媒體」( http://www.vjmedia.com.hk )、「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 )我們的資訊性比較強,有更多咨詢。但是新冒出來的除了「主場新聞」以外其他的很多媒體,他們的政治立場永遠是先行的,在他們那裡看不到甚麼咨詢,只看到他們很鮮明很尖銳的一些觀點。我在大學裡面教書,我的學生很固定去看「獨立媒體」的人不多,但是固定去看「輔仁媒體」的就非常多。一個班裡面大概80%的人都會看,他們不見得很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是他們喜歡看那些很刺激的觀點,例如民粹主義喜歡去罵一些精英,這跟整個香港的氣氛有關,但是他們的內容、資訊含量非常非常少。
黃孫權:這跟台灣也相類似。
葉蔭聰:我覺得這是全球現象。
黃孫權:「自治八樓」的人覺得你們以前寫東西比較有passion,可你們現在的年輕記者越來越像主流媒體的記者,對照片的處理方式跟主流媒體很像。對這個情況,你們有沒有甚麼內部的看法呢?
葉蔭聰:你提到的那些批評,我不能說100%同意,基本上90%是同意的,但是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還沒想出辦法,而且有些東西還要仔細去看,不能說我們永遠就是要跟主流媒體不一樣。有些東西可能主流媒體是好的,我們不一定不能學,不好的地方我們當然要避免或找另外做法。我的確同意我們弄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像一些媒體了,且不說是不是主流媒體,人家自己可能也不覺得自己是主流的,「主場新聞」是不是主流媒體呢?我覺得已經蠻主流了。你說的這些批評也是我們決定要變成一個媒體很容易出現的狀況。我們已經沒辦法所有的人都是acticist(行動者),所以寫出來的東西都是行動者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例如那些出去採訪的實習生,你根本不用教,他就會用一套主流新聞的做法去做,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往後我們要去想我們自己的新聞學是甚麼,這個10年來我們一直沒做得很好,但是現在去談這個東西非常難。因為所謂的主流的媒體也在變,假如我們要有一套不一樣的新聞學,不一樣是跟他們不一樣,那麼他們是誰?他們是甚麼樣?他們自己也在變。以前我們說媒體是堅持一套比較精英的專業的新聞原則,但是現在這個東西已經不存在,現在很多所謂的主流媒體他們的用詞,很像我們以前的學生戰報,比你還更有運動的味道。比如剛才你說的東北(反新界東北開發)的事情,我知道Damon會派不少實習生去做一些可能主流媒體不做的事情。比如說他們比較關心衝突的事件,我們有一部分人會去拍衝突的現場,同時在衝突之前有非常多的報道是關於那些來參加集會的人的採訪。但是很多人包括批評我們的人只看到前者,當然他們也批評的沒錯,我們做的,確實沒有跟其他媒體的差別非常大,但也不能說完全是一樣。我舉一個具體的東北事件的例子,那天晚上在立法會,我們有一個記者拍了示威者之間的矛盾,有些人要拿鐵馬去衝撞立法會,幾個人和一個非常資深的社運人士出來阻擋,他們之間有衝突,我們拍了一個短片是關於這個,也寫了一篇文章出來。此事據我所知主流媒體是沒有報道的,他只報道了示威的人衝擊立法會,但是沒有把內部的那些矛盾、那些動態呈現出來。很有趣的是後來主流媒體報道了這個東西,引用我們的報道,但是已經是第二、三排的報道了,那肯定不是他們的頭條,他們也要過一陣子才會發現。但是社運界對這個東西重不重視,也很難說,那個片子出來之後,有些搞社運的人叫我們不要放這個片子。
黃孫權:破壞運動感情?
葉蔭聰:各種各樣的理由。比如不要把這種矛盾讓人家知道,在片子裡面拍到要衝撞的人的樣子,他們害怕警察找麻煩……好多各種各樣的理由。所以這個事件不那麼簡單,你做了一些跟主流媒體不一樣的東西,也不見得其他人很欣賞,他們希望你跟主流媒體不一樣,但是不是好,也不一定。社運團體希望媒體是喉舌,只說他們要說的話,反而沒有探討是否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在主流媒體和社運團體之外,是不是有另外一種聲音,它是否有價值——這也許是我們的位置。我們已經跟社會運動關係很密切了。東北的事情,我們的焦點都是土地正義聯盟自己的文章,跟他的關係也很密切,但是他們不見得認為我們想法和行動會有價值,反過來只看到你跟主流媒體做的事情很像,這樣的看法也不完全錯,媒體本來就沒那麼簡單。整體來說,我們跟主流媒體還是不一樣的,但是有些做出來的東西的確跟主流媒體很像,到底好不好,要很具體地去看。
黃孫權:現在所有人都可以搞媒體,技術上不是太困難,你們未來有沒有甚麼明確的方向跟計劃?
葉蔭聰:我一直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但是很難實現。從2008年到現在,我們網站的瀏覽量增加了大概四倍,坦白說這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希望更多人去做,不想把自己做大,現在是有點被迫做大。有人說我們還是小媒體,但現在的規模已經比一開始想象的大很多,不論是瀏覽的人數,還是我們的staff,我們從來沒想過要聘三個staff,有更多小型的媒體出現是更重要的。假如香港有很多規模很小的媒體,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做,是一種比較強的公民性而不是政治操作、商業經營,我覺得那就更好。但是過去10年,那種公民性比較強的、非商業的媒體越來越少。2003、2004年的時候比現在多,我們是 survivor(倖存者)。假如說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公民報道的媒體,若有人去做、做得好,我們就讓他去做,沒有人做,我們就要做下去。我們希望很多人去做各種各樣的媒體,我們支持一些小的媒體的計劃,積極掏點錢製作一些社區報,現在有人做社區報,大部分都不是很成功,不管是在社區還是在整個香港的影響力,都還沒有成氣侯。我覺得往後,我們應該要退出來了,不要讓我們越變越大,我們退出來,更多人去做,就是我們的vision。
我覺得往後,我們應該要退出來了,不要讓我們越變越大,我們退出來,更多人去做,就是我們的vision。–葉蔭聰
黃孫權:最後我們談一下財務。
葉蔭聰:從今年看,我們財政的收入60—70%都來自本地的小額捐款,每個人可能每個月捐幾百塊港幣,最少有捐50塊,捐到1000塊港幣的也有,比較少,大概有100多個小額捐款,也要加上每一年「六四」跟「七一」時候的募款。今年相對來說算是募的比較多的,因為找了幾個大咖(梁文道等)來站台,30%我們申請到歐洲一個天主教背景的基金,他資助我們關於媒體政策倡導的項目和一些培訓。每一年的運作經費最主要的開支就是薪水,一年港幣大概60—70萬,最多可能70—80萬,不到100萬港幣。
黃孫權:你們的特約記者要自己準備器材嗎?
葉蔭聰:部分是他們的,我們提供一少部分。有時候不是沒錢買好的器材,而是買完了之後沒有能力管好它。現在比以前要稍微好一些,我們多了一些電腦、相機、錄機,但更多還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黃孫權:請做一個總結,從一開始到現在,是甚麼讓你覺得這事情可以繼續幹下去?
葉蔭聰:我自己比較悲觀,做下去是因為看到越來越少人做我們在做的事情。有些東西對我們是鼓勵,比如我們的影響力,不管是對運動,還是對主流媒體,或是公眾。開始的時候這些所謂專業的記者都看不起我們,我們一開始經常跟記者協會吵架,10年裡前一半都是在吵架,最近這幾年,我們之間關係還不錯,他們也比較承認我們的成果。2006年印象深刻,我跟記者協會的一個主席在大學一個公開的場合吵架,他罵我很凶,我罵他也很凶,但是還好,我們這樣吵,他也不記恨,我也不記恨。10年來吵歸吵鬧歸鬧,我們還是做我們的,至少他們現在比較承認我們的做出來的事情。很明顯,記者協會覺得香港所有媒體都不行,但他們也承認自己沒有做出個像樣子的媒體,所以沒辦法否認我們做的一些事情,儘管他們覺得很有問題。無所謂,邊做邊改。不是說我們做的事情就很完美,我們在好幾個運動裡面都扮演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角色,「天星、皇后碼頭」這個不用說,反高鐵早期沒人關心這個議題的時候,我們在關心,讓整個運動後來有一定的變化。我們做了一些貢獻,這是讓大家認為我們有價值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