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年六月
地點:黑手那卡西辦公室
受訪者:王明惠
訪問者:曾傑
王明惠:哈囉大家好,我是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的團員,我叫王明惠,在2000年加入這個樂隊。
曾傑:王大哥現在從事什麼工作?
王明惠:我退休了,差不多兩年前退休。退休前在台北市停車管理處工作,做管理員。
曾傑:在加入黑手之前就是做這份工作嗎?
王明惠:對。
曾傑:每天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王明惠:每天工作內容就是停車收費,在地下場的話就是每天做一些紀錄跟維修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停車收費。
曾傑:這份工作做了很長時間嗎?
王明惠:二十年。
曾傑:王大哥今年幾歲?
王明惠:62歲。
曾傑:所以你加入黑手的時候差不多50歲左右。
王明惠:對,差不多。
曾傑:那時是什麼契機知道有黑手這個工人樂隊的?
王明惠:這個要從參選後工會幹部開始,因為我們停車管理處那個單位是行政機關嘛,以前照法令來說它不能成立工會,就明定行政機關不能成立工會,後來就有些公益團體幫忙克服了這個難關,我們工會就在民國86年成立了,成立以後我誤打誤撞去參選工會幹部,就選上了,選上以後這些幹部就會被召集起來上勞工教育課,剛好陳柏偉,就是我們那個團長,他在那邊拿著吉他彈彈唱唱,我在那個時候跟他認識,就是在這種機會下他邀請我加入黑手。
曾傑:他那個時候就知道你平常對玩音樂有興趣?
王明惠:我那時候不會玩音樂,我有跟陳柏偉說我不會唱也不會彈,他說可以啊!就在這種情況下加入黑手。
曾傑:你花了多久時間才有第一次的演出?
王明惠:花了多少時間?好像一加入就馬上演出了。
曾傑:就開始唱了。
王明惠:對,就跳跳唱唱了。記得第一次是到台南,成大MP3事件那次,就在那邊開始了。
曾傑:那演奏呢?
王明惠:演奏基本上也是拿吉他,但它沒有插電,就這樣彈就對了(笑)。
曾傑:現在已經會彈了嗎?
王明惠:現在會彈啊,只是拍子不穩。
曾傑:那你的家人呢?你加入黑手前後家人有什麼變化嗎?
王明惠:他們有來看,他們有說你都慢半拍啊,大概是這樣。我感覺彈彈唱唱也滿好的。
曾傑:他們都很支持你加入黑手那卡西。
王明惠:對,總是比去搞工運好吧,工運就是會衝撞到,跟這些官僚有衝撞嘛,這些衝撞他們會擔心會被解僱、被打壓阿,那搞這種文化運動的東西比較沒有那麼直接。
曾傑:那在成為工會幹部之前,有接觸過工人運動嗎?或者是抗爭運動?
王明惠:有啊,就是有參與抗爭才接觸到黑手,因為之前抗爭時我們工人只會拿著大聲公,要嘛拉布條、舉牌啊。加入黑手以後大家會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歌,彈彈唱唱,這個是最大的轉變。
曾傑:那對你的工作內容、工作環境有什麼轉變?
王明惠:工作環境沒有,你是管理員就管理員,不會有改變阿。只是在搞工會幹部這一塊有點改變就是,以前就只會拿大聲公抗爭,後來自己還會唱歌、寫歌來抗爭,那就是最大的轉變了。
曾傑:王大哥你的背景,家裡也是一直都是工人嗎?你的父母親從事什麼職業?
王明惠:我在緬甸出生,大概28歲才來到台灣。
曾傑:你在緬甸出生,所以你的父母親都是台灣人,還是…?
王明惠:我的父母親是廣東人。我們來的時候拿緬甸護照,是屬於難民護照、無國籍護照啦,因為那個時候出去,全部都不能用緬甸籍出去,都要用無國籍護照,當然難民嘛。到後來那些人才准許你可以用緬甸籍出國。
曾傑:所以那時候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所以才…
王明惠:那個時候還沒有戰爭,那時候差不多快要排華了。
曾傑:那為什麼會舉家跑到緬甸去,你又在那邊出生?
王明惠:這個要從我父親那個時候講,就是抗日的時候從雲南那邊隨著部隊到緬甸那邊去阿,那邊有一條中緬公路阿,他們那邊幾乎只剩下這條公路可以有物資運送,等於中國的生命線啦,那個時候那邊駐紮了很多部隊嘛,我父親當工程兵就駐紮在那邊,後來變天了嘛,就有一部分的人來台灣,有一部分回大陸,有一部分留在緬甸,我父親就留在緬甸。
曾傑:那留在緬甸之後呢?還是軍人?
王明惠:沒有沒有,我父親那個時候是經商,他開酒工廠,還有做一些百貨業,還有挖礦、玉那些,經商就對了。
曾傑:那教育呢?到你28歲前…
王明惠:我那個時候在緬甸唸書是念雲南語,後來才改成普通話,後來緬甸政府把那些中文學校收歸國有,又全部都要學緬甸話。之後差不多28歲我就回到澳門去,之前我有到台灣玩過一次,後來居留可以辦很久,我就很努力填表辦,辦成就留下來了。
曾傑:你剛來台灣的時候從事什麼職業?
王明惠:剛到台灣的時候我有開過計程車,後來朋友介紹說停車管理處有在招人,那比較輕鬆阿,可以進來做做看這樣,我一進來做就做了20年。
曾傑:好特別的經歷。接下來我要問一下你怎麼看待黑手那卡西跟社會運動組織的關係?
王明惠:我們工人可以用音樂,把它當做一個武器,能夠掌握多一個武器來跟資方、跟老闆鬥爭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我們到現場抗爭的時候,不可能天天有抗爭,總是有終止的時候,但是這個終點沒關係,因為可以把我們抗爭的故事、聲音用音樂寫成歌,這個抗爭的生命是可以延續的,黑手就是做這一塊,對我來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在於,可以把我以前抗爭的經歷跟故事寫成歌,等於我的抗爭生命得到延續,我會認為最終我們工人只要掌握到文化這一塊,最終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曾傑:你們跟工人階級或是跟工人的關係是什麼樣?
王明惠:關於工人文化這一塊,因為工人最糟糕的就是收入少教育低阿,沒有什麼機會拿樂器、玩樂器啊,這個需要黑手去幫忙推廣,我當然希望我們黑手的音樂可以推廣到每一個工人家庭,事實上這是困難重重,因為這需要資源、需要教育,就是慢慢來阿,就沒有這種條件。在目前來說基本上你叫工人拿起吉他、拿起樂器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曾傑:你2000年的時候加入黑手那卡西,這其實也13、4年了,這13、4年裡你也參與過各種不同的演出嘛,甚至不只是在抗爭現場,也有在校園、做巡迴,今年是不是有去北京表演?有什麼樣的感受?
王明惠:跟大陸那邊的交流,他們的社會背景、組織結構不一樣,感覺到我們這邊的歌好像批判性比較強,大陸那邊社會結構不一樣,如果像我們這樣子的話會馬上面臨危險,不太一樣。他們會比較講一些思鄉阿,那種調子比較強,我們這邊歌曲好像反叛跟批判性比較強。
曾傑:那跟台灣的NGO組織呢?
王明惠:通常邀請就是育麟跟耀婷他們二個人在接洽的,我們基本上是接洽完以後他來跟我們報告,我們是到現場才認識他們,接觸的就是他們嘛,我比較沒有站在第一線工作。
曾傑:但是你到第一線的時候,你跟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你會跟他們聊一聊,然後…
王明惠:會交換一下意見,感覺我們這邊的NGO應該是比較開放一點、民主一點,大陸那邊的話給我的印象就是說他們的組織非常龐大,第一個他們非常年輕,比較有發展的希望,看到這樣我們這邊好像年齡層比較大,都是老的在那邊搞來搞去這樣。
曾傑:那你每一次參與的這些抗爭,你都對他們抗爭議題或他們的看法一致嘛?
王明惠:基本上反正是向統治者挑戰,要改變一定要經過抗爭嘛,但是究竟感覺上是對我們這種抗爭有點懷疑,早就被全世界的資本家看破了我們這種手段,是不是說用傳統的那種工會的力量、社運的力量還有辦法,有點開始在思考這些問題,好像一早就被他們串連起來看破手腳了,過去這種方法不調整不改變好像就不行了,我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曾傑:所以音樂的力量變得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強勢了?
王明惠:音樂的力量當然有發揮它一定的作用,但單靠音樂的力量不夠阿,還要靠工會的力量、社運的力量、NGO的力量都要一起來。
曾傑:你們工會成立之後,有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是推動什麼或是得到什麼樣的勝利嘛?
王明惠:這個講起來抗爭可多了,第一個把我推向不歸路的就是抗爭嘛,90年台北市政府要推動二週工時80小時,原本我們每天在路邊工作是七個鐘頭,他要改成八個半鐘頭,這個是第一戰。還記得很清楚我們把會員召集起來在工會集合,然後我們要步行到停車管理處、步行到市政府去包圍他們,那時候那個處長就找一些流氓阿還有刑警阿,搭著我的肩膀說把這些布條拿下來,牌子不能舉,講了一大堆,後來這個處長親自來跟我講,叫我回來吧,我們才是一家人阿,我前兩天才寫成一首歌,就叫我回來我們才是一家人,你不要被人家利用了,中華商場是我拆的,因為中華商場大家有記憶嘛,西門町那時候最熱鬧的地方,我頭上還縫了30幾針,阿你們這幾百人算什麼,結果被我們這些人一搞,交通局長馬上就來說你們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就當場承諾原來的工作條件不變,那場就到這邊穩住了,就打贏了。
曾傑:那這種抗爭形式後來加到黑手那卡西之後呢?
王明惠:對對,經常就參與黑手有些表演、有些抗爭阿,都是在街頭比較多啦,就去哪裡聲援哪個工會抗爭阿,我就跟著柏偉去唱唱跳跳這樣。
曾傑:其實你才是參與工會組織嘛,然後參與黑手其實有非常長的時間,這麼長的時間,你又有自己的工作,又有家庭,然後非常辛苦的,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一直堅持十幾年?甚至到現在退休之後還一直參與黑手的運作?
王明惠:我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如果我們工人沒有掌握文化這一塊,永遠都不會有希望,因為掌握文化這一塊等於…。抗爭隨時都會終止,不可能天天有抗爭,你要延續抗爭生命只有搞文化鬥爭這一塊,所以我堅持我有一個信念就是說,工人不掌握這一塊永遠都沒有自信,永遠都找不到希望。
曾傑:參與這些運動或在生活上跟你在28歲之前在緬甸生活有什麼差異?
王明惠:基本上沒有,在緬甸的生活幾乎都忘了,來到這邊以前就是靠父母養阿,來到這邊就是要靠親自工作才能生活阿,完全不一樣啦,因為緬甸的生活回不去啦。
曾傑:父母親沒有跟你們一起從緬甸回來?
王明惠:有回來,他們現在留在澳門了,我其實是一個人來台灣。
曾傑:所以時常回去澳門嘛?
王明惠:也沒有時常,這30幾年回去不到10趟吧,我在這邊有家庭、有孩子,都要生活,為了要照顧他們都要工作,跑不太開,而且一個工人的收入有限,回去一趟四個人的機票算一算花費那麼大。
曾傑:那父母親是誰在照顧?
王明惠:我弟弟妹妹,他們有時候也會來台灣。
曾傑:那為什麼當時他們決定留在那裡,那你決定要來台灣?
王明惠:因為我這邊娶老婆啊,她是台灣人。
曾傑:黑手那卡西已經快要20年了,你也參與了10幾年,那你怎麼看黑手那卡西的未來?
王明惠:我有在思考這個問題,以前街頭抗爭通常會去聲援,後來因為台灣工運環境的改變,現在轉型跟學校團體搞一些工作坊,我也在思考說,工運這條路走到這邊好像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有種感覺需要轉變一下、改變一下。
曾傑:所以你覺得目前這種改變的方式是好的嘛?
王明惠:這轉變這條路一定要走的嘛,讓工人能夠掌握到樂器、掌握到這種武器,能夠讓每一個工人能夠用自己的聲音詮釋自己的故事,雖然推動是困難重重,還是要往這方面走。
曾傑:在你身上其實表現得、發展得滿好的,這是一個很典型實踐的例子。
王明惠:是呀,但要讓這種成功經驗發生在別人身上,我一個人當然沒有用阿,要千千萬萬的工人起來才有用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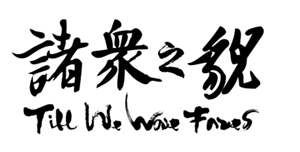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