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年7月1日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富德樓辦公室
受訪者:梁寶山
訪問者:黃孫權
梁寶山:我是梁寶山,以前念藝術專業,加入了「獨立媒體」之後慢慢去搞文化研究,「獨媒」跟我整個想法的改變有很大關系。90年代是過渡時期,1997年前後我主要工作還是在文化藝術,2003年七壹遊行之後,我離開了原來工作的藝術空間,恰恰就有點空,就可以出來做另外的事情。所以那個時候剛好就跟靄雲搞「獨立媒體」,因為大家都是大學同學,就是說那時候也不曉得這是什麽東西,就是壹塊玩嘛,所以最初幾個人而已。但是加入獨立媒體之後,頭幾年都完全是在摸索,我那時候在獨媒的主要角色是把我在文化藝術那一邊的經驗,或者是壹些資源帶過來「獨媒」,因為那時候「獨媒」在香港民間媒體裏面是第壹個。其實很多經驗不單單是從民間媒體帶過來的,其實也有蠻多是搞文化團體的經驗。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棟樓,租的樓嘛,其實原來是我2004年自己工作室先搬進來,然後它的其他單位也慢慢放出來可以租。所以那時候我就說其實「獨立媒體」也可以在這裏申請一個單位。都是剛好2003、2004年,然後「獨立媒體」反而一直呆在那裏,但是我的工作已經不在這裏了。所以這就是兩個場域的一些經驗交換。
黃孫權:妳可不可以談談那時候參加「獨立媒體」,實際在做什麽樣的工作?
梁寶山:2003、2004年,那個時候蠻關鍵的,我在這同一個時期開始的工作就是「夥炭」(http://www.fotanian.org)。「夥炭」是一個藝術家在工廈裏邊的區域,最早幾個視覺藝術的工作室是在2000年開始的,後來他們那時候就邀請我幫忙去統籌,去搞他們每年的開放月。那時候他們都是個別的不同的單位,所以那時候就我去幫忙做了整個區域的mapping。所以現在回頭看蠻重要了,如果是這樣子,就是2004年我是加入了「夥炭」,同時就是「獨立媒體」。完後兩個東西的關系,現在還是若即若離。
黃孫權:2005年妳在幹嘛,就是WTO那年?
梁寶山:WTO那年,就在「獨媒」。那一年其實也是蠻關鍵,因為那時候香港藝術家還沒意識到說藝術參與政治,或者藝術參與社運。但是我現在回頭看,其實WTO那年蠻多藝術家開始關心,然後想不同的辦法去加入社運的運作。
黃孫權:所以妳覺得2005年是香港的社運啟蒙年嗎?
梁寶山:我想那是一個蠻重要的示範的作用,因為反WTO那是很大規模的一個組織,很大規模的global(全球的)的力量,那之前我們做得都很土,規模很小,從來沒想象是可以這樣子有規模的動員,我想主要就是那個quantity(數量)跟quality(質量)的一個轉折吧。
黃孫權:接下來妳就淡出獨立媒體了嗎?
梁寶山:也沒有,我淡出是在2011年左右吧。那時候幾個元素,現在談起來是種瓜得豆。
黃孫權:種瓜得豆?
梁寶山:對,從來都是種瓜得豆,因為我2008年開始蠻花更多時間在我的禪修上,就是佛教那邊。香港藝術圈,其實我想說是社運圈,不過現在都是同一個圈。前幾年也有一個佛教的潮流,剛好那幾年花比較多時間去禪修,因為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做engage Buddhism(左翼佛教)的東西,然後同時間我就開始念博士,所以那時候就想要淡出。但是這就反過來種瓜得豆,反過來2012年就去搞選舉,在立法會選舉。
黃孫權:那麽有什麼印象最深刻妳在獨媒寫的文章,最引起爭議的或最popular的?
梁寶山:最popular的?有,那個時候就在皇后碼頭拆遷運動那時候。因為最後一晚就是像一個大派對嘛,那天你在嗎?那天晚上好多事情發生的,那時候我還有一個身份是藝術家,現在不是了。所以那時候我是三重身份在社運的場合裏邊。那天晚上我還在做行為,我那個行為是在群眾裏邊,我就把西西的《我城》那本書拿出來,然後就找一些想要聽的人,我念給一個人聽,就是一個一個人念。那天晚上剛好有一個人,大家都覺得他是左派,他就在碼頭那邊抗爭,就抗議我們的抗議。大家都在罵他,我就感覺很不好,因為我相信他是真心相信他那些東西。所以我就反過來去他旁邊跟他念書,他是一直不說話,跪在那個碼頭,跪著,我就跟他一直念書。其實主要的目的不是跟他念書,因為我跟他念書其他人就不會來罵他,你懂我意思嗎?那些人都覺得梁寶山把他搞定好了,這樣子就不管他了。所以我就跟他念,大概兩個小時,然後那些人都沒留意他,他才慢慢跟我說話,就這樣子。其實那天很有趣,就是你感覺藝術家裏邊好像是可以break through(攻破)一些東西,跟我單純去做運動是不一樣的事情。所以那之後就寫了篇文章,之後很多反應,大家都反省,或者是繼續對罵也有。對我自己來說那個經驗蠻深刻的,所以我後來出版自己書的時候,也把那個文章也發出去,那幾年就是對我好像剛好就是那個社運跟藝術跟佛教的東西交融的時期。
黃孫權:那篇文章叫什麽題目?妳還有沒有印象?
梁寶山:忘記了!太好了!!
黃孫權:我最近訪問很多團體,我想聽一下妳的想法。因為有一些人覺得獨媒早期那代本身就是運動者,然後又是報導者。但現在新來的一些年輕的記者,他就是比較像volunteers(志願者),或者就像記者。
梁寶山:就是比較制度化,比如說有好多是internship(實習生),很有組織,妳還要帶他們,我們那時候誰帶?自己做,做完之後妳就知道怎麽做,是不一樣。
黃孫權:我遇到一些團體覺得看妳們那一代寫文章是很有熱情的,可是他們現在寫文章就好像是記者在做記者要做的事,就是妳感受不到那個passion,然後文章也比較dry,乾一點。另外一個是,因為「獨立媒體」既是媒體,可是它又像個平臺,因為很多人可以在上面寫東西。所以還是會有些保守的人在上面,妳怎麽看待這兩個事情?
梁寶山:我想可能還是公平點,因為我們那時候都已經,大家都已經30出頭。比如說就是說阿靄(林靄雲)他們,他們做「獨媒」之前已經有很多失敗的經驗,做實體的出版,做運動,做媒體跟運動的一些交叉的東西已經有蠻多失敗的經驗。完後我自己其實第一份打工是報紙的記者,所以大家都已經有好多失敗的經驗。因為我們都是從那些失敗的經驗,投入非常大的熱情跟時間,想要搞一個,自己想要搞的東西,所以就不能比較。跟他們現在的記者比如說念culture studies(文化研究),或者是念創意媒體,他們沒有其他工作的經驗,也沒有失敗的經驗,然後就來到一個已經,也是可以說是非常有制度的平臺上面,我想那個熱情是一定不一樣的。第二個問題,我其實一直覺得那是重要的,比如說有些時候「獨媒」基本上是跟香港社運圈子的關系是一直是蠻好的。因為我們強調的是「獨立」,所以那個「獨立」到底是什麽,我自己覺得獨立不單單是獨立的資本,從政治的establish(建制)的那些事例獨立出來。其實我們跟那些民間團體其實也需要有點距離,不然的話,其實大家都很缺乏就是怎麽回頭看做出來的東西,如果,因為主流媒體不會混在那個圈子裏邊,看到它內部那些問題。但是獨立媒體如果只是同情或者過分投入,也把自己變得跟社運團體是同一口氣,我就覺得有點問題了。。
黃孫權:作為一個文化評論者,這幾年來妳感受到香港的社會文化的一些團體跟所謂媒體之間的關系,有沒有什麽關係是怎麽樣的?
梁寶山:比如說我想起就是我們剛做獨立媒體的時候,我旁邊的朋友怎麽去形容我們在做的東西,然後他們那時候就說他們是一個文化媒體,你懂我意思?所以其實也有一些,總是有一些不對格的東西在裏面,他們是這樣子去理解,因為之前沒有民間報導那些東西,所以他們也是用一個文化的角度去看的。那時候就是我剛才說就是西九龍才剛提出來,整個香港社會氣氛還是,文化藝術那些是蠻邊緣的。我們那個時候伙炭也好,獨媒也好,像這裏富德樓其他的文化團體,也是那時候冒出來的,十年之後你看見現在全部就變非常主流化,我不是說哪個團體,是整個文化主流化。比如我絕對不擔心所謂年輕人不去看藝術、不去看另類的東西,我反而是非常擔心那些古老的東西沒有人看,你說那是後現代的文化轉向的實現,十年之後實現。一方面看是好像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跟你談過,其實恰恰證明就是所有另類迅速地給資本吸收。也不單是資本,比如說是政府對香港文化、身份的論述的吸收。那些所有古跡保育的都是文化的策略去做,那超恐怖,超誇張,那些全部都是十年之前,沒有天星、皇后之前妳是不能想象會發展到這樣子的地步。從我自己個人參與其中的經驗來看,就是所謂社會運動跟文化藝術其實是同一個板塊,如果你宏觀點看整個香港社會的那個轉變是同一個板塊。
黃孫權:所以對妳來說目前看起來非常蓬勃的各種文化的現象是有點危機的,意思是這樣嗎?
梁寶山:因為很困擾,香港到底是開放還是多元?怎麽說,因為比如說我們如果很堅持我們所謂香港角度、香港本土的東西,其實也排斥了很多有趣的東西。但是我想有些時候還是要看不同agent的在權力。
黃孫權:妳剛才談到那個多元跟開放,香港除了有像獨媒以外還有很多所謂的新媒體。
梁寶山:有《主場新聞》、《熱血時報》,就是說看起來好像很多元,可是其實很多反而有點恐怖,所以主流媒體有些是非常,或者《熱血時報》,有一些是非常反中意識的,對不對?
黃孫權:那妳怎麽看待這些,就是妳所謂多元跟開放之間的界限?
梁寶山:也是很有趣,就是你越開放,它們越保守。因為你可以想象從前那種主流媒體,它可以去,怎麽說,國語怎麽說,就是把它扭出來,對吧?我覺得主流媒體總是有一種扭出來的那種魔力在裏邊,但是那些獨立媒體,它就,妳越開放,它就越走極端。你可以看到,可能就是相互的作用,如果沒有那些媒體,或者說沒有那些媒體,八卦網就是,像陳雲那些港獨,或者是本土派的那些聲音,可能也不能太出來。所以很吊詭,真的很吊詭,那時候覺得我們很對,我們做的都是多元,我們做的都是很正義,我們都是幫助弱勢,我們是香港的聲音在哪裏的時候是覺得很對的,但是哎呀,真的是這樣子。
黃孫權:因為那些本土派反中也是香港的聲音的一部分嗎?
梁寶山:對對。因為我常常提出一個批評,主要是文化裏邊,或者說本土派的,就是從電影、普及文化裏邊,甚至於現在的保育運動,其實他們只是美學本土派,那個是非常大的危機。所謂美學本土派就是政府去把那些古跡掏空了,然後給妳一個什麽文化中心,你是覺得很美好的。但是那個本土派是沒有看原來的那個政治經濟結構的,我覺得那個最危險。所以他們去種田那些人,是真的是把本土的那個思路從的經濟運作去重新出發、重新開發。美學本土派我就覺得最壞,他們認為所有”香港派”的電影都是好的,我都莫名其妙,明明是爛得要死,然後妳覺得越低俗就越本土,我是覺得是歪理。
黃孫權:現在臺灣很多人覺得臺灣新電影很好,臺灣喜歡拍什麽環島、廚師…可是臺灣年輕人很愛,說這是本土的、臺灣的。
梁寶山:其實香港都是這樣子,現在,同一個邏輯,所以就……
黃孫權:那怎麽辦,妳有什麽解答嗎?
梁寶山:就罵,我還是有寫的。例如有個團體拿馬會一大筆一大筆的錢,完後就每一趟就是用文化藝術幫他洗太平幣,我就壹直在罵那個人,真的我看那個人很生氣。
黃孫權:有的人說還不如像周思中他們去搞點真的跟土地有關的還比較實在點?
梁寶山:那個還好,我覺得。比如說,另外比如說伙炭,伙炭很多問題,但是因為我跟他們還是蠻有關系,所以我就不是在外面,我就在裏面跟他們不同的人說妳應該怎麽怎麽樣子,是這樣。所以就情況不一樣,反正最近幾年比較回到原來做藝術的那個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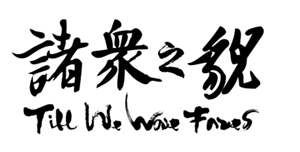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