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拉拉系列之三
當我看到一系列為印度窮困孩子們所編寫的教科書,用各種語言版本來解釋為何月經不是受詛咒,月蝕不是因為怪獸吃了月亮,要如何清潔自己的性器官等等淺顯易懂的文字與圖片。我不禁想到那些免費編纂教科書的們的科學家與大學老師們心中作何思考?他們如何思考理論與實踐改造社會的距離?高大尚的批判理論、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核物理學是科學,對農民婦女來說,可以解決問題的知識才是科學。(黃孫權)
文/劉健芝
甚麼是現代國家的國民?我們會想到國家賦予他們公民權利,他們對國家承擔公民義務,也就是說,現代國民應有能力掌握現代知識與技能,所以,識字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準的其中一個指標。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奮力掃盲卻依然徒勞;國民的「落後」被看成為既是國家落後的結果,也是國家落後的原因。
在印度,情況最惡劣的比哈爾邦,識字率是 47.53%(2001);印度全國平均水準是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卻在十多年前──1991 年 4 月──便已經成為全民識字邦。這個不平凡的數字背後,有一個不平凡的掃盲故事。
1962 年,一批科學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學知識,讓民眾能掌握對他們有用的技能。首先,他們把英語科普讀物翻譯成喀邦語言馬拉亞拉姆語。「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就這樣誕生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1978 年在全國 990 個鄉之中的 600 個鄉,逐步成立了「農村科學論壇」,目的是與村民一起嘗試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喀科運」的構想,是每個村莊有兩三名「喀科運」的活躍成員,對當地問題有具體細緻的瞭解,帶動村民建設社區。
經過幾年實踐,「喀科運」發現,幾名活躍成員可以起帶頭作用,但社區整體發展必須靠民眾積極參與,尤其是最底層的人、最邊緣的人不能被遺棄。1986 年,「喀科運」調整策略,將重點放在推動全民識字,讓識字的人不只學懂看書讀報,還培養能力掌握知識,創造知識,以改造他們生存的環境。「喀科運」決議在五年內令喀邦全民識字,於是籌畫一個行動綱領,送交印度國家教育部。試點建議在十七萬人口的安那庫林區(Ernakulam)進行。國家掃盲委員會在 1988 年審批撥款。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為「喀科運」從未肩負這麼大的專案,國家掃盲委員會也從未將這類工作交給一個民間志願團體來推行。
「喀科運」的計畫,是在該區動員一萬五千名志願者進行為期一年的掃盲活動。這種龐大的動員史無前例。上街示威、罷工抗議之類的行動是印度公民慣常見到的,但大量義工動員做社會公益事業,則出乎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意料。1989年試點工作開始進行,同時,「喀科運」組織文藝演出隊,巡迴到全邦 1600 多個地點作宣傳,印製、售賣大量小冊子,宣揚與掃盲、發展、自治相關的理念。
1990 年 2 月,安那庫林區宣佈成為全印度第一個全民識字區,參與的義工有 2萬 3 千名。試驗非常成功,旋即在全邦開展,動員 30 萬志願者;1991 年 4 月,喀邦成為全民識字邦。國家掃盲委員會非常讚賞這個成績,邀請「喀科運」和「全印度民眾科學聯網」(「全印科聯」)協助在全國推行掃盲運動。為此,「全印科聯」專門成立一個教育機構,名為「知識與智慧促進會」(BGVS),在接著的幾年,在全國多個邦約 400 個區推行掃盲運動,報名參與掃盲運動的學員有 1 億 2千萬人,報名的義工有 1 千萬人,實際完成比例甚高。
數位固然可觀,但掃盲運動的真義不在量,而在質。「喀科運」的出發點,並不把文盲的村民看成愚昧無知、缺乏教養。相反,他們相信民眾之間流傳寶貴的民間智慧,人人有學習能力、應變能力。現代社會的大小事務總離不開文字,民眾識字,能更有自信參與,能更好地譜寫自己的歷史。
這個出發點非常重要,與一般的現代化、都市化社會的主流觀點迥異;它不把農民看成落後可恥,看成現代化的絆腳石、包袱,而是正視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犧牲被邊緣化的遭遇,對非西方國家在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統治下沒有甚麼選擇餘地而接受的西方發展模式,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它看到這樣的發展是狂妄的,滿足的只是少數得益者偏執的欲望,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命卻被嚴重破壞,從包裹大氣層的臭氧層到海洋深處到地下水,都受到不可逆轉的污染破壞,同時,社會分化和地區衝突也隨著所謂科技發達文明進步而日益嚴重,越來越看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有必要抗衡這種狂妄。
這個問題涉及的不單單是農民的出路;全社會的出路也在農民身上。因此,他們要協助農民在自身、在社區、在本地,尋找力量尋找資源,改變生活中不如意不合理之處,扭轉狂妄自大、不懂節制的欲望所推動的發展之路。他們的發展觀以民為本,以大多數人利益為依歸。
帶著這種理念推行的掃盲運動,重點是個人及社區的長遠變化。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內洛爾區(Nellore),一些農村婦女參加掃盲班,每週聚會。掃盲班不少教材是學員表達興趣和需要後,與教員合編或改寫;在一地編寫的教材會在各地流傳。這就是說,掃盲班並沒有呆板地規定學員學懂甚麼字,才算符合「脫盲」標準,而是讓教材和學習靈活配合學員的處境。
內洛爾區的掃盲運動在 1990 年 1 月宣佈開展,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宣傳推廣──主辦者組織歌舞創作、街頭劇團、家訪等等,到各村各戶動員教員和學員志願參與。1991 年 1 月,掃盲班正式上課。在杜巴貢德村(Dubagunta),學員有三本教材,其中一本有一個《絲妲的故事》,說的是絲妲的丈夫酗酒,她無法改變丈夫的惡習,自殺了。杜巴貢德村的掃盲班婦女學員,讀到這個故事時百感交集,紛紛訴說她們自己的故事。59 歲的玉婷(Uddin)說,她的丈夫 14 年前被酒精奪命,死前經常酒醉鬧事。在這個貧窮的農村,自然環境惡劣,農作物經常被颱風摧毀,失業普遍,更糟糕的是,僅有的一點錢,常被男人拿去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後虐打妻兒。
掃盲班的婦女,訴說各自的不幸,有的說,丈夫打她有了新的理由,就是她這麼大歲數,還要甚麼脫盲識字,是瘋了。婦女們商議後,決意村內不留一個酒鬼,於是行動起來。她們的故事迅速傳到其它村落,也很快寫入掃盲讀本;新的故事叫《如果婦女們團結起來》。這一課說:「這不是虛構的故事,這是我們上掃盲夜課的婦女的成就。我們的村叫杜巴貢德村。我們用血汗賺取工資,從土裡生產金子,但有甚麼用?錢都花在土酒上,我們的男人沒有錢買酒,就賣掉家裡的米、油、任何東西...我們的日子很難過。後來我們讀到絲妲的故事,我們開始想,弄死她的是甚麼...第二天,我們幾百人走到村口,截停一輛酒車,叫商人把酒倒掉,我們一人拿出一盧比賠償他的損失。他嚇怕了。就是這樣,那天以後,再沒有滴酒進村...我們現在有力量,也有信心。我們知道只有通過教育,我們才能取得這次勝利。」

印度中央邦,BGVS的年度學習成果聚會(圖/諸重之貌,取自即將發行的BGVS紀錄片)

印度中央邦,BGVS的年度學習成果聚會(圖/諸重之貌,取自即將發行的BGVS紀錄片)
在之後的村民自治選舉中,玉婷被選上村委主任,這在重男輕女的農村,是不簡單的。如星火燎原,各地婦女紛紛起來反對土酒。在 1992 年的民間反酒運動壓力下,邦政府在 1993 年宣佈全面禁酒。在裡貢達伯度村(Leguntapadu),一名政府官員應邀參加反酒集會時,問婦女能否一天儲蓄一盧比。一名婦女上前,把一盧比放入他手裡,其它婦女紛紛效法。官員問,為甚麼把錢給我,為甚麼你們不組成小組,把儲蓄集起來,自己管理?儲蓄運動從這個村開始發展,超過 20 萬名婦女自發組織了婦女儲蓄小組,接著逐漸有能力以集體名義向銀行或信用社貸款。
印度有許多世界銀行、聯合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等搞的小額貸款項目,但前述例子主要不同之處,是這些自發的婦女小組,是經過掃盲運動一段時期的個人能力和集體意識的培育之後,從婦女自身面對的日常問題出發,尋求解決。掌握知識、增加自信、維護尊嚴,是內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反土酒運動和婦女儲蓄小組運動,是由掃盲運動引發的。喀拉拉邦帶頭開展的掃盲運動,最可貴的是它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讓全民成為有知有識之士,這個目標是全社會接受的;運動實際開展之時,也捲入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政府官員、不同黨派人士和科技專才,充當義務教員,在與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學員共處的期間,打破隔膜,消除誤解,增進相互的認識。掃盲運動推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整合和社區發展動力的開發。也因此,掃盲運動並不以民眾脫盲而結束,而是全社區成員進一步捲入對社區本地資源的瞭解、探測、開發。鄉村建設運動不僅有了本地骨幹人才帶頭,有了廣大民眾參與,也有了凝聚建設運動的公理人心和人際網路。掃盲運動奠下基石,讓民間自發的社區規劃行動可以開展,也讓1996 年史無前例的喀拉拉邦「人民計畫運動」得以推行。
這裡的「發展」,綜合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它首先是一場文化運動,一場人的提升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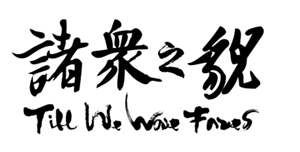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