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孫權
2016年1月23日,下了捷運走了長長一段雨路,我陌生地到達了橋下公共空間但顯然成為私營地的酒吧。這應該是20年來唯一「爆滿」的「黑手」演唱會了。也是樂迷平均年齡最大,熟識的老朋友最多的一場演唱會了,光在門口抽煙就遇到了何東洪,楊祖珺,陳光興,鐘喬等舊識。在《破報》解散時我曾自嘲說過,我們應該在孩子20歲前就殺死他,避免他們如成人般的腐敗勢利,終究變成跟曾經反抗過的人一樣。笑語總是箴言。我帶領「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資料庫」計畫中為黑手拍的紀錄片:《福氣個屁!工人樂隊黑手那卡西》,片尾的集體採訪與對談笑容竟然真的成為歷史了。
內鬥的文化團體不知何幾,但很少有文化團體自己出來搞個「崩解」演唱會,告知親朋好友,黑手結束了。顯然的,這是一種抵抗繼續這樣下去的信念,對黑手自身15週年演唱會「就這樣辦!」的反對,重新回到黑手11週年演唱會的自我提問「該怎麼辦?」。至於為何要抵抗「就這麼辦」的原因,外人只能從臉書網絡上的輕浮煙火窺見局部,黑手成員鬧翻了,跟工委會,火盟/民陣,選舉路線,團員民主參與,集體決策,督導員制度等等有關。演唱會上,黑手三位成員禁語,不做解釋。認真地一首首唱著,回顧著黑手20年來的經典歌曲,就彷若回顧我們這一代社會抗爭的歷史。抗爭會過去,音樂成迴響。但歷史總是回應著抗爭的,歷史總是一直回應著反對繼續這樣,「就這麼辦!」的力量。
黑手從工運的伴唱那卡西,開始學習與工人一起做音樂,最後變成與諸眾(樂生院民,性工作者,工殤團體,移工群體,外配,精障者)一起做音樂,最後透過團體互訪互唱,開始勾連不同群體的意識,將被壓迫者的處境政治化,一般化,直指結構的壓迫而非個人與少數族群之命運蹉怨。一路上,他們就是社會運動而非為伴奏者,他們直接參與了「新人」的製造,開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意義上的「新的野蠻人」的創造力,從窮人與被壓迫者中製作相互的愛。難道這不就顯示了諸眾不是已然存在(being),而是等著被製造的(making),不是具形具貌的身體(body),而是逃逸,拒絕,出走的小鮮肉(living fresh)。
既是如此,放棄已成形貌的身體也不可惜。黑手應該放棄黑手,或說,成為黑手們,成為院民,成為性工作者,成為工殤者,成為外勞外配外人,成為精障視障肢障者,成為更多更多的黑的,模糊不清但持續不斷的聲音。黑手與那卡西本來取用了台灣大眾熟悉之名,現在也僅僅將共用名稱回給台灣大眾而已。黑手解不解散,分不分手,分成幾個黑手,是不是那卡西,其實我一點都不關心,難道這世界上左翼的分裂爭吵還是新鮮事嗎?世上最難的是革命後的第一天,而我們離得還遠著呢。
這是不再有先鋒黨的時代了,不再需要有代表。簡單來說,就是拋棄生物權力(bio-power)規訓完全的身體,拒絕這個曾經聽從指令,服從權力,左右派知識分子與所有文明人、市民都難逃的政治社會構造與權力體制的身體,崩解成可以自我增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之實踐,賤民之實踐,諸眾之實踐,窮人婦女黑人之實踐,實踐就是生產。這正是這場演出的黑手三人拒絕黑手團隊11週年演唱會的真正力量。更重要的,一個個生命政治是在共同的(in common)的行動中將其殊異性(singularity)變成諸眾的,一如黑手以團體形式曾經示範過的那樣。現在,只是他們要重新在踽踽獨行的實踐中創造共同而已。
表演最後,三位黑手成員回顧完經典歌曲後,回到「個人創作」時間更讓我有此感覺。陳伯偉的〈原來我們在一起是這個意思〉有著年輕時候的自嘲,〈起來〉更是振奮人心。張迪皓〈左派廢話〉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濁水溪肛門時期的味道,楊友仁的〈富士康左轉〉則一樣有英式吉他牆和複雜編曲的風格。都好,都好,只要不要重複團體黑手已然成形的身體都好。
其實,抗爭不就只是將應許之地的共享財產從私有化那裡爭奪回來而已嗎?黑手這三位團員做的事情也是這樣如此而已。
(原刊於2016二月號 今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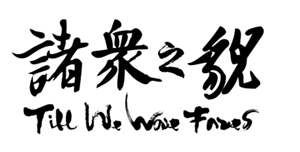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