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陳隆昊,唐山書店、唐山出版社創辦人。解嚴前的1982年開始大量藉由翻版引進批判性書籍與西方思潮,為當時威權統治下,思想自由被箝制、經濟能力尚負擔不起原文書的台灣、東亞與東南亞知識份子提供了重要的知識管道。同時支持各種思想、文學上另類書籍的出版與發行,唐山書店三十多年來成為各種實驗文學、左翼理論、人文思潮的基地。
>
訪談者:曾傑、甘志雨 訪談地點:唐山書版社倉庫,台北市大安區,台灣 訪談時間:2016.05.14 整理校對:甘志雨 編輯:黃孫權、曾傑
曾: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談談小時候的生活是怎麼樣子的?
陳:小的時候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覺得我們過著富裕的生活。關西姓陳的有兩個比較大的家族,我們家是其中一個。在那個年代,我們說「有地斯有財」,所謂的大家族就是擁有比較大面積的土地,都是地主。我們家那時候算是地主階級,所以小的時候我們家有很多別人沒有的東西,譬如說我的叔叔騎著一部義大利進口的摩托車(Vespa),那時候台灣還沒多少摩托車呢。家裡面也是很早就有了電視、冰箱,這些東西台灣還沒有生產,而是向美國人買,美國人當然有冰箱、電視啦,我們就向美軍買來轉賣給老百姓。那時候你想要擁有電視還得要牌照,那年頭什麼東西都要執照。
曾:那時候街頭巷尾的人會來你家看電視嗎?
陳:對,那時候台灣還是個國家啊,不像現在國不成國。舉辦亞洲盃棒球賽、籃球賽的時候,很多人就會來看實況轉播。小的時候我不懂籃球,只記得有個國手叫作卜樹仁(前裕隆男籃成員),因為我不懂規則,還以為有一個人要一直站在籃框旁邊什麼的,電視裡頭一直叫他的名字,我本來以為他是像棒球的壘側指導教練,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球員。
曾:陳老闆是什麼時候離開關西的?
陳:我初中就離開關西了。當時國民政府開始實施了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一連串的土地改革措施,這一波下來我們家就什麼都沒有了,也就落魄了。
曾:當時你們家族有多少人呢?
陳:我的老家其實保養得非常好,但我們家不是那種官宦之家,就只是一般民宅,到現在都還保存下來。我的曾曾祖父、曾祖父是關係地區的私塾老師,不是什麼官就只是教書的,經過了很多代的累積,才擁有了許多土地。不只是我這一房而已,其他親戚也是經過了很多代的耕耘成了當地的地主。
曾:父親也是讀書人嗎?
陳:現在很多有錢人不是都會把小孩送到澳洲、英國念書嗎,我父親年紀比較大,戰前日本統治時期,我的姑媽、大姑丈都被送到日本念書。當時夏威夷有很多日裔美國人,所以他們兩夫婦也成了夏威夷人,後來也回日本去教英文。我的祖父將我父親安排寄宿在他們家,所以我父親說得一口流利的美國腔英文。我記得我那時候的美國同學,在台大念書的時候最喜歡到我家來玩,他說去別人家玩苦得要命,大家講臺語都聽不懂,講國語又卡卡得,還是到我家來最舒服,可以說英文,因為我父親可以跟她說英文。這就像是台灣很多家庭把小孩送到國外去一樣,父親在日本畢業於明治大學,他的身分證上寫得是明治大學商學院商科,可是他做生意卻總是失敗啊!
曾:父親做過什麼生意呢?
陳:父親在土地改革之後,終究還是有一點底,不致於完全活不下去。以前父親的工作就是靠著家裡的地產去收租,說到底就是個「壞地主」,靠著收佃農的地租賺錢。我有時候覺得老天很公平呀,這就是所謂的「現世報」。我們家族靠收人家租金維生,不知道父親算不算的上一個仁慈的地主,但這些錢都是從佃農家裡挖出來的。我的書店也是得赴房租,付得我苦得要死啊,所以我就想了一個名詞,我就是一個「佃商」。
農業社會的時候,農人叫佃農,耕耘著別人的土地;現在到了工商社會,那時是有地斯有財,現在城市裡面就成了「有房斯有財」,像我書店的大樓,一樓到七樓都是同一個人所有。他把地下室租給我6萬,一樓租給八方雲集十幾萬,二樓以上租給科見美語,這房東可不只一棟房子呀,南門市場也有、士林也有、內湖也有。所以他累積財富很快,非常快。所以我才說現世報,我從地主階級變成了一個小佃商。我覺得(馬克思)還是厲害,他看到剝削與被剝削的本質是不會變的,不管社會怎麼進化永遠有人剝削你、有人被剝削,就和蘋果的工廠一樣,蘋果不會直接剝削你,但他透過鴻海(富士康)去剝削而已,道理是一樣的。
曾:小的時候地主的小孩會和佃農的孩子一起玩嗎?
陳:不會,因為階級的關係,家裡不讓我跟他們接觸,他大概怕我跟他有感情的時候呢,搞不好還怕我愛上哪個小女生,這不就麻雀遍鳳凰了嘛,反正階級就是這樣子。就像印度的種性制度,你不可能從賤民變成婆羅門,不可能跨越那差距。
曾: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你離開關西之後的事情。
陳:關西是在台三線上,關西算是附屬的地區,如果注意一下台灣的交通,台一線是在平地上的、台三線則是靠山,沿著中央山脈邊的就是台三線。台三線周遭的聚落都是鄉鎮,大部分是「鎮」,從板橋鎮開始一路往南,大溪、三峽、龍潭、關西、竹東都是鎮,一路連到東勢鎮。反而台一線上的只是「鄉」。
- 編註:1950年台灣頒佈的地方自治法明定,5萬人以下聚落稱作鄉、10-15萬人稱作鎮、15萬人以上稱作市
為什麼當時靠山的地帶比較有錢你知道嗎?因為靠山吃山,山都是經濟作物,種橘子,樟腦、茶葉這些。尤其是日本人來了以後,透過日本全世界的商業管道,可以把我們的茶葉賣到美國、英國。不是流傳說英國女王喝了東方來的茶,說是東方美人嘛(Oriental Beauty),東方美人茶就是我們客家人做的。茶葉照理是一心二葉,要是葉子被蟲吃了照理是不能用的,我們客家人很節省,被蟲吃了照樣做茶葉,沒想要那些被咬過的茶有一種特殊的香味。當時這茶葉還沒有名字,出口之後,被英國女王喝了,從此就叫做「東方美人茶」啦。
總之呢,關西靠山的鄉鎮後來漸漸沒落,本來主要靠的是樟腦,後來樟腦也被化學的東西取代了;茶葉也是一樣,英國人不想被日本人扣稅,就不在台灣種了,改到印度英國人自己的地方去,還能省下運費,我們的市場一下子就沒有了,日本人的世界網絡再怎麼樣也不會比英國強,不會比法國強,人家可是老資本主義國家。
曾:你們家的地基本是租給種茶的佃農嗎?
陳:都有,平地也有種稻的,要看什麼地適合種什麼東西。關西有平地也有小坡、小丘陵,山的出口我們蓋了一棟小洋房,這些佃農帶著農產扛著出來的時候都要在小洋房那兒秤過,接著就是三七分帳,他們拿三、我們拿七。我們家呢住在關西街上,陳家有很多洋房、洋樓,其他親戚也都住在洋房裡,但關西人口比較少,後來漸漸沒落。相較之下,關西往新竹會先經過新埔,新埔當時工商業比較發達,算是山裡出來的人們的集散地。祖父的弟弟(叔公),叔公他也曾留學日本,還考上日本的司法官,日本戰敗之後就回來台灣。他當時對國民黨很火大,所以不願意去當「官」,就決定教書,後來就成了新埔中學的校長。祖父就把我這個孫子送去新埔,我就住在這個叔公校長的家裡。
甘:那是初中還是高中?
陳:初中,我那時候還小哪懂什麼事啊,過去新埔的第一個禮拜,我媽媽來看我,她就偷偷地哭呀,因為他看我連洗澡都不會,洗不乾淨,以前在家裡都是媽媽幫我們洗澡,去了新埔我連頭都不知道怎麼洗。那時我還不知道她為什麼哭,還問他:「媽媽媽媽,發生什麼事情你在哭啊。」我媽說,你這傻子我就疼惜你,你還問我為什麼哭。沒辦法嘛,就是到了一個陌生的城鎮,雖然就在隔壁,但當時交通狀況各方面不是那麼好,不像現在巴士很多一搭20分鐘就到了,而且沒有家裡的允許也不敢回家。
祖父那時候想說我這個孫子送去那邊,看可不可以好好念書。因為戰後嬰兒潮的關係,那個年代升學考試很激烈,想要考上大學錄取率很低,文科10幾%、理工科也不過就20幾%,10個人只有一個人能考上大學,而且還不是什麼台大,而是考上比較後段的文化、世新之類的私立學校。那時候學校很少,就算是考上銘傳、實踐也都是很優秀的人才。
當時我們鄉下有些人功課很好,被送去台北念建中,可是到了建中的時候就學壞啦。例如說我有個輩分一樣、年紀也一樣的堂弟,他考上建中到了台北之後跟別人一起租房子,然後就沉迷上了打麻將。他後來還是考上了醫科,可是一輩子都在賭博,很可惜啊,他一有空就是賭博。我從初中畢業之後,一方面我成績沒那麼好,二方面家裡捨不得,就要我考竹中,所以就留下來了。
曾:那你在新埔有學壞嗎?
陳: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我一直對閱讀有興趣。我在新埔的時候,成天瞎晃,要是當時我找了同儕們哈菸,那我可能就完蛋了對不對,就在我我就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剛好轉進去新埔的一間書店。那間書店是當時很典型的「書局」專門賣參考書的,還有發行商會配給你一些出版品、文具什麼的,轉進去之後,我看到了一本書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我就買了下來。

甘:你一個初中生還買這種書!
陳:還不只啊,這本書花了我一個月生活費的一大部分。也許我剛好買對書了,初二之後基本上閱讀已經沒有困難了,你知道男生嘛對這種書特別感興趣,一看到瓜地馬拉戰役、巴丹島戰役,看得爽的不得了啊!從那時候開始就覺得讀書很快樂,有了一個念頭是,我沒有朋友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大事,書就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喜歡看書到什麼程度呢?我的生活費沒有很多,所以不能一直買書,鄉下也沒那麼多書。直到我發現中學的圖書館裡頭有很多書,我記得很清楚,民國40-50年代,台灣還有很多國家資本的公司,當時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超過70%,譬如說中國石油、台泥什麼的都是國家資本的公司。中國石油當時出版一份刊物叫做《拾穗》,當時對版權不是那麼重視,這刊物就把西方新知、人文、科技什麼的翻譯成中文,每月出版一本。我在圖書館看到這雜誌,覺得這書真好啊,會介紹各種類型的知識,我問了圖書館小姐知道《拾穗》每個月5號會到,從此之後我每個月5號下課就會跑到圖書館翻閱這些刊物。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那時候剛好是以阿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沒多久,以色列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從北邊佔領了戈蘭高地(Golan Height))接著就把約旦西岸佔領了,還一路打到了約旦河,也佔領了南邊的加薩走廊(Gaza)。六日戰爭之後,《拾穗》介紹了當時的地上部隊的「獨眼龍」將軍,後來還當上了總理(編註:當時主導六日戰爭的是以色列的戴揚將軍[Moše Dajan],他曾擔任以色列的國防部長、教育部長,並未擔任總理),我記得當時他負責攻打埃及那一側,當時有個西方記者報導這場戰爭,其中有一段報導震撼了我一生。那個記者寫道,以阿戰爭的時候軍官死的比士兵還多,一般來說戰場的死傷是正三角形,越高階的軍人死傷程度越少,結果在這場戰役裡面是一個倒三角形。
記者注意到這個情況就問了獨眼龍將軍,他說,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能打贏這場戰爭?因為你如果只叫小兵往前衝,軍官在後面,這樣誰會跟你衝啊,所以我們軍官都在前面衝鋒。這一場戰爭對以色列來說是存亡之際,當時全部的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這一仗是多麼重要啊,就是軍官帶頭衝鋒,我們才能打贏戰爭的。我一直記著這句話,我說,以後我當了老闆,也要帶頭衝,這樣才能贏。所以後來我做了這一行,常常需要搬書,一包一包的書,員工們搬兩包書,我為了做榜樣對不對,就搬三包、四包,就這樣長期下來才把自己的膝蓋磨壞了。所以我常常說,這個獨眼龍將軍誤我一生。


曾:陳老闆中學喜歡讀課外書,這樣擅長考試嗎?
陳:不擅於考試呢,當時老師跟我說你就考,建中大概是沒希望了,運氣好的話能讀附中,再不行就是成功高中;家裡聽到我要去台北念書覺得不方便,就要我去考竹中。那個年代竹中還算是不錯的,是桃竹苗地區最好的學校,也就這樣考上了竹中,讀了新竹中學。那時候竹中可沒有住宿啊,得要每天通車。你知道多可憐嗎?一大早就起床,直達車太貴了我們坐不起,就搭普通車,每一站都停。上學的時候每一站都有學生上車,新竹中學、新竹女中、新竹工業學校、新竹高商等等,那段日子我印象很深刻,從關西經過新埔到、竹北到六家。現在六家很繁榮,都是高樓大廈,有時候想說如果我的祖先們不是在關西開墾,而是在竹北發展的話,雖然竹北可能競爭比較激烈,開墾的面積可能沒有那麼大,甚至得要自己幹活。但這樣就不會被耕者有其田啦對不對,現在竹北不是有很多暴發戶嘛,幾分地就能賣上好幾千萬、好幾億,我們家偏偏在關西搞了這麼多地,最後呢全部都被政府收掉啦。
曾:所以那個時候你在唸高中的時候,家裡就已經沒什麼錢了?
陳:沒有錢了,我父親本來職業是地主,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工作,變成了無業遊民,很多人看到我家還有一點本錢,就一直拐我爸爸去做生意,投資這個、投資那個。你知道,投資你如說沒有親自去掌管,別人跟你說陪光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陪光了還是假的?
曾:你印象中父親投資了什麼行業?
陳:我跟你講,我父親當時投資了一個生意,我到今天都覺得其實他是對的。你知道是什麼嗎?「充電」。你看現在全部的東西都在充電對不對,手機啊什麼的都要充電,我父親那時候就投資了充電廠。當時美軍駐台,有時候會在關西演習,走的時候就把充電的手電筒送給了一個關西的年輕小伙子。那個年輕小伙子很聰明,他就把手電筒拆開來,把充電的部份研究清楚,當時充電這個概念很不成熟,他把充電零件拆開來之後,就跟我爸爸說這東西有錢賺,我爸爸也覺得這很有前途。確實是啊,今天有什麼東西不充電啊。
曾:有點太超越時代了。
陳:對!有時候覺得說,你走在時代的前端,來的早還不如來得巧。有時候真的是這個樣子,你來得太早,那個時代沒有很多電器,還搞什麼充電,你看現在人手一支手機,我們天天要充電。我爸爸當時投資充電器的,那個小伙子叫做阿純,阿純出技術我父親出錢,錢都被阿純騙光了,一連投資了好幾個事業,本來生活就已經不那麼好過了,最後來賠光了,我的成長過程就是一直往弱勢移動。
曾:不管怎麼說你還算是個知識分子吧,接下你不是考上了台大念了人類學,這對你們家來說算是重大的事情吧?
陳:沒有沒有,你知道我們家雖然是垮掉的一代,但家族裡頭小孩子要去讀書的觀念完全沒有變,雖說變窮了,但窮還是要讀書。我家裡就是我這一代和我的上一代,光我們陳家大概有20幾個醫生,我對於人文的東西實在太有興趣了,那時候最希望小孩當醫生,他們都考的上但我考不上。
曾:你要念人類學的時候,家裡人沒有反對嗎?
陳:我家裡不但反對,把我罵的抬不起頭,我爸爸覺得我違背了他希望我學醫的心願,他借新埔叔公的口說:「你念個人類學就是吃屎的意思。」我還是個沒有自信的小孩子,這對我打擊很大。父親可能覺得不好意思自己說出口,就說是叔公說得。在他們腦中覺得有出息就是要當醫生、念理工科啦,他們也這樣鼓勵小孩子,這樣說來我們家族可是很厲害的,你看看滿地的醫生。
曾:那麼你的兄弟姊妹呢?
陳:我家垮掉之後,我上大學的時候很慘啊,整天打工。當時讀書的時候不想增加爸爸媽媽的負擔,不只是不想成為家裡的負擔,還希望弟弟妹妹上學不用爸媽出錢,為此我什麼都幹,甚至在公館擺地攤。我大一大二的時候功課很好,整天讀書,當時台大有「書卷獎」一個班5%,50個人的班級就是3個人,人類學20幾個人的班級大概就是兩名,他會頒給你一個獎章,現在我還留著。有的時候我覺得,因為我是家裡的老大,所以責任感很重,當年的台灣經濟不像現在這樣,滿街都是銀行,當時除了三商銀只有合作金庫、土地銀行等等,要借錢多難啊。我們家也沒有土地可以抵押,能抵押都是些山坡地,人家看了也不想借給你。但是我父親的生意一直需要錢,最好借錢的就是左鄰右舍,他們都覺得陳家這麼有錢,借錢給他們一定不用擔心。我父親到處借錢,有一回我回鄉下去,早上10點多,我問媽媽說你怎麼還沒去買菜,她回答我現在她不趕出去買菜、不太敢出門,她說走到市場很多人跟他要錢,有的時候只能託隔壁的去買,一直被催討很沒面子,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也生不出錢來還債。那次回到台北,我對讀書的希望就完全幻滅了,我只想要打工賺錢,當家教啊什麼的,什麼都幹。
曾:擺地攤時都賣些什麼東西?
陳:當時我有一個經濟系同學,她家裡是在中部開成衣廠,成衣廠時場會有一些樣品,打樣、規格不對的衣服等等。那時候我就賣這些衣服,很便宜能賣就賣。當年還沒什麼擺地攤的概念,我算是很早就開始擺地攤的,在公館擺攤沒有警察會抓你,公館也沒有現在這麼熱鬧。那時候這個同學從家裡搬來這一大堆樣品衣,幾乎都是不要錢的,我們就賣三件一百,當年鈔票最高面值就是一百元,還沒有五百、一千的鈔票,每天10點多收攤,書包裡滿滿的都是一百塊鈔票,我們就在附近冰店的角落數錢,二一分帳把錢分了。
那時候賺錢,多多少少能拿一點回去給媽媽,怕她捨不得,我當然不敢跟她說我擺地攤,只好說我在當家教。後來這些樣品衣賣完了,朋友又介紹我去實踐賣做衣服的雜誌,當時人們還會自己做衣服,我媽媽就會自己做衣服。這時候就不是擺地攤了,我們在辛亥路跟羅斯福路轉角的地方,有間叫做「登麗美安」的裁縫補習班(這棟房子已經拆掉了),很多人在裡面學裁縫,生意好的不得了。我們在裡頭賣書,賣《裝苑》那種雜誌,過期沒人買了我就去倉庫買過來,賣給這些補習班的人。我那時候滿腦子都是賺錢的念頭,滿腦子靈光,想到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鑽,我們還批了衣大堆這種雜誌去服飾店賣,那些服飾店只有學生跟老師賣的不過癮,還到銘傳、實踐大學去賣,不但賣得很好,還趁機認識了很多漂亮的女生。
當時賣東西,我們都對外說我們是「臺大的」,當做宣傳口號。大三開始因為我都在賣東西賺錢,成績就一落千丈,有一次很巧,平常我都在外面賣書,不曉得為什麼那天我跑到系館去,看到每個人都在念書,我就問他們:「你們怎麼都在念書?」他們說待會兒要期末考了。人類學系的學生很少,那堂課是大三跟大四一起修的,大四生要畢業了所以期末考就提前,所以大三也要一起考試。幸好那天我去了系館,要不然就糟糕了。

大學時期的陳隆昊
曾:既然這樣,為什麼大學畢業之後沒有直接開始做生意,反而還繼續念了研究所呢?
陳:因為我心裡想的是說我終於可以讀書,不讀書只是暫時的狀態,我什麼都不會,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長得這麼矮,小小的,別的都不會只會讀書。
曾:家裡發生了什麼變化讓你覺得又可以讀書了?
陳:我是想說有一天我賺夠了錢就好。當時幾乎全班畢業都出國繼續念書,我知道我不可能出國,那對家裡負擔太大,我不但早早就放棄出國的想法,連書都沒有讀了。並不是不想讀,而是不可能繼續讀了。大了大四的時候,我去找我的恩師-李亦園,他生前是中研院院士,每年三節都會去看他。他老年失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去看他也不敢去太久,每次都去個半小時,他會問我:「你老大呢?」,過一會兒又問:「你老大呢?」每次去都是同一句話一直問。
曾:當時他怎麼影響您?
陳:我現在對東南亞很有興趣就是因為他,當年我修了東南亞民族誌的課程,當年課本都是盜版的,開學了要印課本,這堂課的學生很少,印刷店老闆說印20幾本他不印,我問了印刷店說要一百本才印。我對李老師說了這件事,李老師就把這堂開放成大一到研究生一起修,才能印出課本來。當然啦,印刷店一定會多印幾本,這樣他還可以賣別人。不知道是不是我有特別的功勞,李老師給我的期末分數是大學部裡最高的,他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這堂課的期末報告,我寫的題目是〈錫與馬來西亞〉,討論馬來西亞重要的錫礦產業,他還把這篇文章登到了《思與言》雜誌,李老師是真的非常照顧我。
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去找他,對他說我很想出國,但是家裡狀況這樣實在沒辦法,想要繼續念書的話只能在國內念。那個年頭全台灣只有台大有人類學,而且只有碩士學位,沒有博士班。李先生告訴我,不能出國就念國內的研究所,但我擔心念研究所的經濟負擔也很大,他說國內的研究所只要念的是公立的,不但免學雜費還會給薪水,我才去考了研究所。我後來念了政治大學的邊政所(現為民族學所),我去註冊的時候,還得繳60幾塊,我問註冊小姐:「不是免學雜費嗎?為什麼還要繳60幾塊?」她回答我:「總不能保險費還要我們幫你出吧!」
曾:60幾塊那時候很多嗎?
陳:不多啦,60幾塊如果拿去吃簡餐,大概可以吃三頓。當研究生每個月可以領兩千元,那時候兩千塊很爽了,省省地用,除了吃飯前還能拿來買書。李先生對我說等到博士班成立,你就再去考博士班。研究所的時候我就在南天書局打工,整天幫他做盜版書,南天書局當時還沒有門市,出版社就是他家,在牯嶺街那邊。我的工作是幫他一條龍的生產,去圖書館借書,拿去印刷廠把書拆開來一頁一頁照相製版,在裝訂回去還回圖書館。
曾:所以圖書館破破爛爛的書就是因為有你嗎?
陳:你要看看是不是我盜版的,可能還有別家,不能都怪我,還有很多個。
曾:那時候在南天書局打工領多少錢?
陳:我那時候跟他(南天書局老闆)某種程度是合夥,他跟我講說,負責這件事情,賣到的錢我們兩個一起分。念研究所的時候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當時同學8個人,到了第三年,7個同學都畢業了,我因為太忙了根本沒寫論文,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作延畢,回家去被我媽媽罵死了。鄉下嘛,家裡的孩子上大學總是會讓街坊吃醋,又讀到研究所醋勁更重了,這下子逮到機會,媽媽一到街上去,三姑六婆們就說讀大學還會「留級」,藉機恥笑我。我媽媽在家就罵我說你在幹什麼!現在想起來,我根本就是延畢的先行者。第三年之後我就跟老闆說我不能再幫你忙了,辭掉了工作,花了一年時間專心寫論文,整整讀了四年才畢業。
曾:畢業之後就沒想再唸書了嗎?
陳:因為我在南天幹這個阿,就覺得盜版不錯阿,很好賺阿。
曾:當時賣一本盜版書可以賺多少錢?
陳:我跟你講南天的情況,到了我那時候(唐山書店時期)就比較差了,因為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生產成本提高很多。南天那年頭,台灣做什麼行業都很容易變成一個大公司,不管是做螺絲啦、衣服啦,後來都變成大企業,等到我畢業那時就晚了,研究所畢業後經歷了石油危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南天的老闆出一套《明代名人傳》,總共分兩冊,一本主文、一本目錄。你知道這本書定價多少錢嗎?1,000元!批給同行打七折、700元,最大的客人是美國學生。當年有很多美國學生來台念書,台大裡頭有一個史丹佛中心,是美國常春藤聯盟的幾個名校一起組織的,讓想從事漢語研究、學中文的學生來這裡念書,畢竟想學漢語、漢文在這邊效果比在美國好很多,所以就來了很多美國學生。當時這些學生看到什麼盜版書就寫信回去說:《明代名人傳》出來了,研究明史的人就登記請他們代購,學生來買就賣800元,那時候800元等於20塊美金,那本書在美國賣120元美金,你看省了多少錢,學生看到這麼便宜就先買了再說,書都運到國外去了。
曾:那時候這種書成本多少錢呢?
陳:跟剛剛說得一樣,定價1,000元,賣給同行700元,賣給學生800元,成本卻只要192元,你看多好賺啊!當年深坑一層40坪公寓只要90萬,20-30坪的公寓賣75萬,光是《明代名人傳》就算都只賣700,一本可以賺500元,總共印了500套,全部賣完就可以賺到25萬,這當然是低估啦。一套書賣掉就可以買三分之一棟房子,相比之下我們現在幹了一輩子也只能買一間廁所。就是因為看到這行業這麼好賺,我畢業之後才覺得幹嘛還要搞東搞西,才投入這行。不過因為石油危機,成本翻了一倍,本來192塊的成本變成350塊,沒那麼好賺了;房價也跟著上漲,逐漸賺的追不上了,現在賣一套這種書,可能只能買一台腳踏車了。
曾:那們你的弟妹們呢?他們後來怎麼了?
陳:我們家的負債都是我叔公、祖父背負,大家把該賣的賣一賣都還清了,不是父親還的而是家族還的。還清之後,家裡不知道還能做什麼,當時我舅舅在美國念書後就住在美國了,他就說不然都到美國來好了,當時不少留學生去了美國賺錢養家,一家也就搬過去了。我們家也一樣全家搬去美國,但我已經讀高中十幾歲了,因為兵役的關係,我不能跟著家裡搬過去。弟弟後來就在美國念書,去了密西根大學念數學,現在也在外國公司工作,沒有回台灣了。妹妹則是在美國念資訊工程,後來在UCLA教書,認識了一個在哈佛念生化的,兩人結婚之後,國內鼓勵海外人才回流,妹妹和妹婿就回台灣,現在在中研院分子生物所當研究員。
曾:全家移民的時候,你年紀還小,是誰在台灣照顧你呢?
陳:主要是靠家族的力量,我的叔叔、叔公、祖父母。高中畢業讀大學離家去了,念完研究所、當兵,後來就搞唐山、幹盜版。那時候台大、清大都設了人類學的博士班,但我想都不想,做生意去囉。我要跟你們說一件重要的事情,後來生意越來越難做,不能盜版之後只能出版,出版的成本很高,書這行業就更難做了,那時候我想說算了我還是去讀書吧。但是我不想考國內的研究所,畢竟我以前的同學們都在當所長了,我要是沒考上不就笑死人,這麼老了去考還考不過一些小學地、小學妹;想要出國,還是沒有錢,我一輩子都跟前不太有緣份。後來我打算去考公費留學,結果查了一下,發現45歲以上就不能考公費了,這條規則不知道還在不在,我想他們是覺得國家出錢讓你出去念書,結果妳讀完就退休,這樣投資效益太差了。那時候,我已經45歲了,沒得念只能放棄,你看看我的學生歷程很悲慘的,我就跟「盜版書」一樣。
曾:唐山時代你盜版的書,你自己讀嗎?
陳:我跟你講,每個行業有每個行業的重點,你若是從事研究你就要整本書看完;那我們賣書的人怎麼看書呢?前言看一看、目錄看一看、每個小節大概翻一下,人家問我的時候不會完全答不出來就好,至少讀者問起來你可以講個重點讓他想買。你知道嗎,六一二大限的時候,我正在拼命印書,其他老闆們都已經賺了大錢買房子了,我那時候賺的還不夠,必須不斷地投入,當時印了100多種書,突然六月大限,雖然既往不咎,但是所有已經批出去的書得要全部買回來,你若是不買下游的書店威脅說要告你,我只好掏錢買回來。100、200多種書籍,分布在各大學、周遭的書店裡,紛紛要退書給我,我花了好大一筆錢。
曾:這些書現在在哪裡呢?
陳:我下次帶你去看,在另外一個倉庫。我一直捨不得丟阿,你知道客家人的文化有所謂的「敬字亭」,書院、廟宇旁邊都有一個專用的爐,寫字的紙張不能亂丟,要在這爐裡燒,像天公說明這些紙張沒用了。那些盜版書呢,我捨不得丟但也不能賣,所以遇到有什麼同學喜歡讀書,就會送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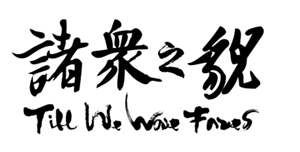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輩分,非備份
節制,非截至
收攤,非收貪
感謝!已修正。
難天書局,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