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陳隆昊,唐山書店、唐山出版社創辦人。1982年解嚴前開始大量藉由翻版引進批判性書籍與西方思潮,為當時威權統治下,思想自由被箝制、經濟能力尚負擔不起原文書的台灣、東亞與東南亞知識份子提供了重要的知識管道。同時支持各種思想、文學上另類書籍的出版與發行,唐山書店三十多年來遂成為各種實驗文學、左翼理論、人文思潮的基地。

訪談者:曾傑、甘志雨 訪談地點:唐山書版社倉庫,台北市大安區,台灣 訪談時間:2016.07.23 整理校對:甘志雨
曾: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幾個比較重要的人,比如說你跟夏鑄九老師是怎麼認識的?
陳:那時候台大還沒有城鄉所,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叫做「都市計畫規劃室」,屬於土木系的一個研究單位,老夏那時候就是土木計畫規劃室的老師,開的課當然就是一些都市研究的課。那時候老夏他說他下學期要上一門課,拿給我(一本書),那是MIT的老師Kevin Lynch,當時的書名還叫做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一個好城市的理論),後來這本書在版時就把Theory拿掉了,就叫做《Good City Form》。我就從第一版的《Theory of Good City Form》開始盜版,一直盜版到改成《Good City Form》,好幾年老師上課都用Lynch這本書。我記得第一年的時候他叫我印,我也沒有去問都市計畫規劃室到底有多少學生,不過土木系的人很多,很多土木系的人去修這門課,因為建築跟都市關係很密切。我記得那一年,助教打電話來說:我們登記好了,一共要我記得是兩百多本。哇,我爽得不得了,一次喔!

唐山早期翻版之原文書
曾:那是哪一年?
陳:那很久了,我也查不出來。大概就是1983.84年我開始盜版的那時候啦,也是規劃室大概剛開始的時候。我就印,就賣了好幾百本,一個學期學生就兩三百人。
曾:那時候賣這樣一本可以賺多少錢?
陳:很好賺啊,第一個,我不用付什麼版稅、稿費,我也不用排版、編輯啊,什麼都不用,那現成的書就拿去印刷廠照相製版,那個年代的生產成本也都還很低,台灣物價相對是低的時候。書價跟現在比,現在也沒有貴到太多,可能那時候是兩、三百塊,現在就是四、五百塊這樣子,所以其實蠻好賺的。後來夏老師上的課本幾乎都是我幫他盜版,後來變成城鄉所以後課很多。老實說因為那時候我盜版的書,不是微積分、醫學那種的,我印的書還是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那可能老師就這樣拿給我,可能我也比較不會去計算說可以賺多少錢,所以跟夏老師就變成也是亦師亦友。後來他給我最重要的一個幫助就是,夏老師翻譯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之崛起》等那一套書,夏老師規劃那一套書,我們幫他出版,唐山出版。那一套書算是我出版生命裡面很重要的。

唐山出版Manuel Castells《信息時代三部曲》,夏鑄九等譯
曾:那套書是不是絕版了?
陳:沒有絕版,還有書。不過後來因為也有大陸版,台灣很多賣簡體書的也進口了簡體版的,那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因為那其實有區域限制(territory),就是說我只能在台灣賣,他們只能在大陸賣,他們不應該拿到這邊來賣。不過他們拿來賣因為便宜啊,那時候甚至有學生跑下來說「我要買《網絡社會之崛起》。」,我說我有啊,他說「啊不是這個,我是要買簡體版的。」,因為那便宜很多嘛,後來就沒那麼好賣了。
是我出版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三本一大套,又是Castells,算是一本很有名的書嘛。後來夏老師這一路,他自己的作品也都是我出版的。而且講真的,我也很感謝夏老師,你知道嗎,他都沒有跟我收版稅,他都是免費給我印。一般老師還是會收版稅,他都沒跟我要,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然夏老師他的地位啦,他做的事情更多更重要,都沒有跟我收版稅很不好意思啦。
曾:他哪一本書賣得最好?
陳:他自己的書都差不多,都是學生會用的,算是好賣。他退休之後又把最近十年的論文整理過以後,陸陸續續我們又幫他出了後面一套,五六本書。書名很怪,我都念不出來,什麼異質啊、結構啊。那些書大概年底以前會全部出齊,出齊以後我就準備幫夏老師辦一個…
曾:簽書會之類的?
陳:對,現在還可以,再十年學生可能都不知道老夏是誰了,現在像你們都還有聽過他課或是怎麼樣的。所以我準備年底幫他在台北、台中、高雄辦。
曾:巡迴簽書。
陳:對,也算是對他一個巡禮吧,因為他一路做田野工作、做調查跑很多地方。所以這就是夏老師。
曾:你跟陳光興老師是怎麼認識?
陳:我跟光興他們,就是現在亞太研究室…以前他們最早有一批進步的…那時候還不是老師,那時候裡面可能還有研究生,比較進步的、左派的、對於社會運動、學運、性別有很強烈的意識的一些朋友,最早他們就搞了《島嶼邊緣》雜誌。那一批比較進步的老師,現在他們基本上都在學院裡面。他們很會寫東西的就辦了《島嶼邊緣》。哇,那時候《島嶼邊緣》是引領風騷,後來因為那些老師們之間有思想性的摩擦,就結束了,大概出到第十二、十三期。我最遺憾的就是那十幾期,我當時每一期都賣光,到最後我一本都沒有留,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蒐齊,搞不好還要去舊書店找。

《島嶼邊緣》雜誌
曾:那時候是他們來找你,請你印的嗎?
陳:那時候也是一樣,我就是盜版這些比較進步思潮的書,所以他們就覺得臭氣相投。那時候呢,杭之,叫陳忠信,規劃了一個叫做「唐山論叢」,就是專門出學術性的書,思潮性的書。他們同時也搞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老夏、陳光興都是台社。台社出版以後我也幫它經銷,很好賣。島嶼邊緣沒有了以後就是台社,那時間上有沒有重疊我不是很記得。
當然台社後來的走向越來越,因為學術要求SSCI認證,文章要在那種期刊才算分,因為這樣後來台社就走入很學術的方向,當然市場就慢慢差了,因為那是非常論文的東西,雖然也是關心社會議題,只是一般人就不會看了,變成學術論文的形式。當然也因為台灣社會變遷,刊物越來越多,選擇性也多,所以後來銷售就降低成幾百本。剛開始的時候,我記得第二期是老夏主編的,也是關於城鄉那些概念的文章,那一期兩千本賣完喔,後來還再版,期刊還可以這樣子,好厲害。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曾:那前面島嶼邊緣大概賣多少?
陳:一千多兩千,就是都賣完啦,現在你要賣三百、五百本都很困難。我跟光興就這樣一路因為學術期刊的關係。台社本來是他們出錢,我經銷,後來變成他們編好,我出印刷費,變成這樣是我也承擔一點啦,到現在出一百多期了,一個學術期刊能出一百多期,而且不是什麼台大的期刊,算是民間的,也算是一個奇蹟,我也覺得我要分擔一些費用。
曾:還有誰?譬如你最早是在南天書局打工,南天老闆是誰?
陳:還是一樣,魏先生。他大我八歲,他看起來精神比我還好,我搬書搬到這邊不行那邊不行。他的書局,他兒子要接,他七十三歲了。因為我們是同鄉,我那時候家裡經濟不是很好,需要錢,他剛開南天書局、出版社,我就去幫他,那時候我在讀研究所,所有的盜版書都是我去圖書館借出來的,印好就把它裝回去再還回去。我就從研究所開始打工,所以我被老師貼了標籤,說我是不專心讀書、都在打工的學生,當然寫報告什麼的我還是會硬著交,但不是很認真的寫。其實我那時在政大就被認為是不認真的學生。到了研三的時候我們八個同學都畢業了,就我一個人還在那邊唸,回鄉下就被我媽媽罵,說鄉下三姑六婆說怎麼讀大學還有留級的,我被罵得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後來回來我就跟南天的魏老闆辭職,研四就專心寫論文,花了一年的時間把它趕出來,當然寫一年是很草率的啦。到後來才知道,原來我不過就是延畢嘛,哪是什麼留級。
曾:所以你是在南天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印刷、出版這些工作的?
陳:當然,我在南天把做出版的十八般武藝都全學會了,我必須要跑印刷廠、跑裝訂場、跑製版場,到現在我都還可以自己做書耶。像是精裝的書,要切多少紙板,後面膠布要多少,要怎麼黏回去,我都會做。我也很想在退休後,專門幫人家修復壞掉的老書。
曾:這搞不好是需要的。
陳:是有需要的,像是在中和的國立台灣圖書館,他們都有修書的部門,有專門的師父在修。
曾:那時候你可以介入南天要盜版什麼書嗎?
陳:很大的程度是我決定的,當然有時候是有些老師說要印什麼書、用什麼課本,我就跑去圖書館看有沒有書,有就借出來。
曾:那時候南天印的都是什麼樣的書?
陳:那時候剛好是美國跟中國建交(民國61年)後,美國的學生瀰漫著一股中國熱,做中國研究突然變成顯學。那時候美國瀰漫一股中國熱,我記得那時候我盜版一套叫做《明代名人傳》,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有一對研究生夫婦終其一生,他的論文就是把明代名人做傳記,英文的,就出了那本書。我就盜版,印了600套,沒有多久就賣光光了!
曾:歷史系學生來買的?
陳:不是,你知道那時候美國學生有史丹佛中心、師大國語中心,那些學生就是要做中國研究才來學中文,他們可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可能是UCLA的學生,就私下傳播「台灣現在有盜版什麼英文書。」他們在美國就登記,比方說哈佛大學中國史的班上就登記了20套,然後耶魯的,各個大學就登記,他們就叫在台灣的同學買,再寄回去。600套沒有多久就賣完了耶,現在我看賣兩套都不容易。主要是英文的,其實是很大的出口轉外銷。
曾:像這種賣盜版的錢要扣稅嗎?
陳:當然,要開發票就要繳稅呀。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學生直接來南天買,八折。他們還是覺得很便宜,明代名人傳一套我記得美金原價是$125,那時候是40比1,所以算起來是四、五千塊。可是那時候台灣我們訂價一套一千塊,他們學生買還八折,那同業批書,比方說雙葉批是七折。所以一套800塊,對美國學生來講省很多,就買了一批又一批寄回去。所以我在南天的時候,像這些書我要拿去印刷廠,要做這些事情,還要叫裝訂場把書裝回去我要還回圖書館,
曾:那你後來要開書店時,南天老闆不會覺得競爭嗎?
陳:好,你聽我講。那時候中國研究是非常熱的,現在的話大家不會客氣,那個時候我的方向是社會科學,我還算是上一世代的人,我不想跟魏老闆競爭,我想說我應該要走一個自己的、另外的方向。當然我的基礎、老師、我熟悉的還是中國研究,而且那時候中國研究是多麼熱啊,但是我那時候就選擇做社會科學,所以我就盜版社會學、政治學這些學科的書。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到底要翻什麼書好,我就去找中研院啊、民族所的那些同學,問什麼書可以翻譯的,最早的兩本書,一本是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遠流那套新潮譯叢有翻譯。另一本是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這兩本書都是大概1976年得到美國的社會學會的索羅金獎,每年的社會學會會頒發當年最有價值的書,我在中研院的同學說這兩本都是得索羅金獎的,不用擔心它的學術品質,所以我就翻版,跟他走不一樣的路,不要跟老闆搶生意。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y Cliff Geertz
曾:你早期開書店都沒有遇到競爭上的問題嗎?書店之間彼此競爭。
陳:當然有,社會科學也不是只有我,像雙葉是一個大的翻譯集團,是什麼都印,商科的也印、理工科的也印、文科的也印。我們當時很好玩,各印各的。比如說哈伯瑪斯的《Legitimation Crisis》,他印我也印,那我們這些盜版商還沒有文明到大家坐下來分配,就發現說他也印我也印,那也沒辦法,就各印各的,頂多就是大家互相把價錢調成一樣。當然不會有五六家在印啦,可能一般就同時有兩家,可能這本書我跟一家衝到了,那本書他跟另一家衝到了,書太多了偶爾會發生這種事情。
曾: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人?
陳:我這二十年基本上接觸的是學者,這些老師他們商業的氣息很淡,我做這一行最高興的,我記得當時要從鄉下要上台北讀書的時候,我祖父把我叫到跟前告誡我「你到台北去要注意身體,不要為了省錢把身體弄壞了。人哪,最大的四個慾望:吃喝嫖賭。吃的跟喝的你不要省,但是嫖跟賭絕對不要去碰,一碰一生可能就完蛋了。」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小孩,所以一輩子就…,像我去Las Vegas就頂多丟一個quarter,就一個,拉一下,我很清楚那的機率喔,他賭場作莊的都算好了,最後你一定輸的,當然有些人剛好碰到錢掉下來啦。那我覺得最高興的是,認識這些學者、大學老師不計其數,可能幾百個,最高興的就是大家喝杯咖啡,或者吃一頓簡餐,就可以了。我從來沒有夜生活,我都回家,沒有機會啦,我不是搞建築啊那些大生意,林森北路那些都沒去過,就是跟老師在這附近的餐廳吃個飯這樣。
曾:那除了老夏、光興之外,有沒有特別應該要提的?
陳:有一個叫石計生老師,他是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另一個叫做高榮禧老師,後來去巴黎大學念了相關的學位。他們現在都在台灣當教授,我特別提他們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長期在紫藤廬開美學、哲學的課程,免費的、長期的,可能已經二十年了,隔幾個禮拜就在那邊開美學的課程。他們的精神我很感佩,而他們的書也都給我出,也沒有收版稅。
曾:所以你出了很多老師的書?
陳:我出版的書基本上都是老師的,因為我都出學術性的書嘛,本來是不應該一直書學術性的書,因為市場太小,可是我就是一直出。
曾:那有沒有一些寄賣作品的,像是詩集、小說的作家是值得提的?比如說閻鴻亞?
陳:鴻鴻當年還年輕,剛從法國回來,他們就搞現代詩,現在搞一個叫做《現在詩》,他現在自己做出版,黑眼睛,有做劇團也有出版。鴻鴻的書,《現在詩》都是我在經銷,他就代表《現在詩》來跟我結帳。我那時候自己看店,他打給我我們就見面,兩個不是做生意的人在那邊算帳,有時候要算好久。鴻鴻那時候也幫我很大的忙,弄他的詩集,他也幫我介紹了很多寫詩的朋友,在我這裡出版。當然因為詩集的銷售不好,鴻鴻會跟他們講說,唐山可以幫你出版,但是你要自己去籌出版經費,所以我也沒什麼太大的風險,就幫很多現在詩圈子裏面的朋友出版。
鴻鴻那時候還幫我一個很大的忙,因為他也是教戲劇的,他覺得需要一些西方的劇本,因為教戲劇需要劇本,所以他幫我用唐山的名字申請一套《當代經典劇作譯叢》,通通都是戲劇界的老師友情贊助來翻譯,我們就去申請國藝會的出版計畫,那年我們本來計畫出一套四十本的劇本,兩百萬,後來國藝會下來的經費只有八十萬,八十萬不可能出四十本,光印刷費就不只了,還要翻譯費,不可能。後來鴻鴻就幫我跟國藝會減成二十本,本來是想說放棄,不過八十萬也是一筆錢,變成說自己得想辦法貼一點錢,鴻鴻就說沒關係,出了以後他會去幫我找各個學校戲劇課上課用,所以我們就做了。那一年國藝會的補助最高的我記得是優劇場,大概一兩百萬,我們八十萬是第二名,那時候八十萬很多了,十幾二十年前。就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還是把它勉強接下來,做出來了。
曾:那時候印了幾套?
陳:大概一千套,一千是印刷廠的底線,我們也覺得一千套是頂了,不能再多了,萬一賣不出去怎麼辦。所以鴻鴻老師給我很大的幫忙,也是很重要的。像台社啦、劇本啦或是夏老師的書,都是我在出版過程裡比較重要的,人生總是這樣,總是有些東西可以提出來的。
曾:這些也是盜版的嗎?
陳:沒有,全部都有花錢跟國外申請版權的,所以你看八十萬出二十本,一本才四萬,頂多是夠版權啊翻譯費,還好劇本文字不是那麼多,所以翻譯費也不是那麼多,其他印刷費就是自己出了,還好鴻鴻老師幫我找很多的學校,陸續有賣完,有些還再版。那時候選的書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一些得獎的桂冠作家的劇本。
曾:有沒有那種以前寄賣詩集、小說集的作家,後來成名的?
陳:說真的,我出版這些東西,從一開始大家都知道是比較邊緣的,比較非主流的。要說詩集,最有名的就是夏宇,不能說我幫她出書,因為夏宇的書都是自己做的,她很有實驗精神,每次出書的封面啊、內頁的設計都一直變化,所以她喜歡自己做,我是幫她經銷,也是因為她是《現在詩》的一員。當時她的書給我經銷,老實講還不是那麼有名氣,那時候誠品還沒有幾家,它也是專門在賣很特別的、很有藝術設計感的書為主,所以他們就把我放在他們書店最好的位置,當然那時候夏宇也開始有名氣了。我記得那時候很多媒體都報導夏宇的詩集怎麼樣好看,有一年7-11推出旅行閱讀,比方你搭火車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竟然有推薦夏宇的詩集,好幾次下來,讓夏宇的詩集非常好賣,我幫她賣她最有名的《腹語術》,我想應該是上萬本。後來就陸續到現在,後來也有幫她經銷,但就沒那麼多了。

夏宇《腹語術》
曾:幫人家經銷,抽成比例多少?
陳:我們大多都是小眾的,量不大,所以大概是一成到兩成之間,看我發給誰,博客來或誠品大概就一成,一般的書店大概就一成半到兩成。這是毛利,我們還是有些成本。我也是沒什麼賺,但就大家互相幫忙。你說一些詩集其實沒人要發,大的發行商沒人要做這事情,總要有人願意做。
曾:你跟夏宇老師現在還有聯繫嗎?
陳:本來夏宇老師就很神秘,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那種神秘感也對她的詩集有幫助,有段時間她住在法國,有時候到法屬的一個島上。
曾:夏宇老師很有錢嗎,怎麼能這樣跑?
陳:我覺得是人的風格問題,寫作有時候在家裡可能寫不出來,比方說毛姆,他好像是到新加坡還是泰國才寫出來,因為背景、風格,海明威是在古巴寫作。寫作有時是一個氛圍,或是找他的寫作背景。
曾:我記得你是1982年開始…
陳:盜版,82年開始盜版,84年開書店。
曾:那時候美麗島事件已經過很久了吧,美麗島1979年。
陳:也不算很久啦,我那時候剛好當兵在部隊裡面,那時候整個營區瘋狂的批判,我也不得不起來表態啊,說美麗島這些人是壞份子,誰敢說他們是…哈哈。那有點像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沒有人敢講真心話。
曾:那後來你開書店後,有沒有跟這些那時候還是黨外的人有接觸?
陳:我跟他們沒有在政治上…,他們會到唐山來買書。國民黨也有認真的,像周陽山也會來買書,民進黨那時候黨外嘛,像林濁水、邱義仁啦,鄭麗君那時候還是進步的學生,他們都會來買書。
曾:他們會特別要求要買被禁的書嗎?
陳:倒是沒有,就是在書店裡看有什麼書,當然有些書我沒有他們會問我。那時候執政黨也是會來書店來監察,因為我們書店算是個各方人馬都會來的地方,以前一個客人下來,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便衣,他可能看書看半天,是在看有誰在這,各種情形都有。
曾:那有發生過什麼有趣的事情?
陳:我一開始是賣所謂的黑書,就是被禁的書,一般的黑書都是在發財車賣的,他們開著發財車賣,比方說禮拜一在東海,禮拜二在逢甲,就在門口賣,大部分是這樣的,也有像在台大門口擺攤子的施先生,很有名的,也是賣禁書,他是個老先生,他也不怕,警備總部也拿他沒辦法。那我書店賣這些書算是膽子比較大的,但那時候我書店不可能不賣這種書,我不賣這種書就不是一個社會科學、人文的專業書店,我賣的時候就知道他們會來沒收,所以這種禁書就不要多,每次三本這樣賣,賣完了我再去後面拿,那他們下來就沒收三本,我本來也就預計會被沒收,不可能一本都沒有,他可能反而逼得你更緊,後來我算一算他們好像到了要交報告就會來,因為沒收才有成績,台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西方的社會,他們來會開一張沒收單。
有一次他下來,我一看就知道,因為久了就知道那些人。但這次不一樣,以前是在我書店的平台找,這次直接就走到後面去,哇我嚇一跳,趕緊跟進去,我就是在後面的倉庫,不會亂放,是放在一個箱子裡面,他居然知道是哪個箱子,全部拿出來,每種都拿了幾十本啊,我就知道死定了,那次沒收了好幾百本走。我後來想說只有一種可能,我的工讀生被收買了,當然一開始很氣,一次幾百本,那些不是我盜版的,是人家拿來給我的,我也不能說被沒收了就不給人家錢,我本來想要查是誰,是哪個工讀生幹的好事,後來…我想這就是讀書的意義,我記得阿多諾在納粹時代也是替納粹講話,你沒有逃走就不得不講嘛,不然就沒命了。我當然很氣啊,想知道是哪個傢伙,後來想想說不定這個小朋友…你知道國民黨很高竿,說不定跟他說「你爸爸逃漏稅喔,你幫我做這件事,漏稅的事就一筆勾銷」,可能有這個情形,當時某種程度還是個獨裁政權之下,人民有時候是被迫的,我就沒有查。我想這就是讀書的意義吧,想事情會比較周延一點。
曾:1991年野百合,他們在中正廟前面集會你有去參加嗎?那時候夏老師他們也都跑去講話。
陳:我有去看,可是我沒有去參加靜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覺得我可以關心政治,可是我不要牽涉(involve)進去政治裡面,畢竟我要做生意嘛,這是我的一個原則。第二個算是很現實的問題,我那時候沒有很多工讀生,大多自己看店,那時候他們都跑光光了我生意很難做,我找不到工讀生欸,但我店還是要開,所以我就沒有去。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中正紀念堂抗爭的時候,我生意差到一天沒有兩個客人來,等於說我的客人全部都對那有興趣,不管有沒有去靜坐或是去看熱鬧,那幾天生意簡直差到爆。這一次318有一天我們也關門,因為工讀生說要去,我總不能讓他們一輩子遺憾,太多人要請假了,乾脆關店一天。
曾:那野百合之後你生意有變好嗎?有更多人想要看左翼的書嗎?
陳:我開書店的時候是各種運動,不管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開始蓬勃的時候,所以我那時候生意真的是一路向上揚,當然野百合更加深了這個,而且那時候有個氛圍就是他們要做各種行動,他們就會想到要看書,看人家歐美是怎麼弄的,看這種時候要怎麼去抗爭,或是說思想上的路線應該要怎麼抓穩,所以確實是有。
曾:那你有因為這些事件特別去選要印什麼書嗎?
陳:講真的我一路上都受到影響,所以從各種運動的書、工會的書,我那時候也印了幾本工會的書,後來慢慢馬克思的書也曾經很熱門,後來共產國家垮台就轉向了,變成例如女性主義的書,有一陣子也流行後現代。每一個流行都會影響到我們盜版或出版書的方向。
曾:你從來都沒印過資本論嗎?
陳:沒有,資本論很大一套,印了大概也沒幾個人買,後來我有印馬恩選四本,那資本論有很多經濟學的計算,一般人可能比較難…後來時報出了以後就更沒有必要出了。當然那時候要印的話也只能用大陸的,大陸出版社在這種時候會很注意他是要給誰,因為資本論是他們的國學,那時報要印他們就會同意,因為時報的實力堅強,品質、銷售面都會比較完整,那我們小不點的他們可能還覺得不夠格,而我們也不可能全部自己找人翻譯,要用別人的版本,所以諸多考量下沒有出。
曾:你們後來搞獨立書店聯盟,是誰提議的?
陳:那是階段性的,一開始就是在我們附近,溫羅汀。那時候主要是城鄉所的康旻杰老師對這事很關心。那時候郝龍斌當台北市長時,文化局長就找了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主要是這兩個老師,文化局想要promote(宣傳)台北的文化,就想說要在這邊搞一些活動。康老師對這種社區的事情很有心,就找了這些獨立書店,其實那時候希望溫羅汀代表著獨立書店,還有咖啡廳,咖啡廳是文人、學者重要的集會場地,比方說以前的明星咖啡廳。另外就是NGO,我們這邊有很多基金會,各種團體。就希望這個地區能夠形塑出特色來,確實也不是故意去形塑,是本來就有的,後來就變成這個溫羅汀。但是到最後還是書店比較認真去參與,咖啡廳,我們有在咖啡廳辦一些講座等等,他們當然沒有我們書店那麼有寂寞感,因為我們生意不好嘛,所以我們幾個書店就比較有參與,當然我算是比較積極的參與。
這幾年溫羅汀也闖出一點名號,很巧的是溫羅汀跟西門町在都市裡是一個很好的對比,一個是年輕人的天堂,一個是讀書人的聚落。這兩三年因為溫羅汀,因為台電想要敦親睦鄰,他想要先把大學里打下來,因為都是教授嘛,他們做了很多活動,就這樣搞起來。前不久我去見一個朋友,車子停下來聽到一個老先生在問「溫羅汀在哪裡?」我非常感動,但路人說他不知道,我剛好在趕路,就跟他說你往台大公館那方向走。後來我後悔了,應該跟我朋友說我晚一點到,因為溫羅汀不是一個真正的地名,只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而已,我怕他到時候找不到很痛苦,我走了有點後悔。甚至有一次我坐日航,雜誌上還有介紹溫羅汀,有一次看報紙在蓋房子,其實離台大蠻遠的,也宣傳說我們在溫羅汀,這總是好事。

「溫羅汀獨立書店聯盟」臉書專頁
曾:那這個聯盟,你跟其他的老闆,比如說晶晶書庫的老闆是好朋友嗎?
陳:晶晶書庫以前是阿哲,現在換了,我不太跟他來往,他們現在不賣書了,賣雜誌而已。女書店、或是南天這種很獨立書店的有,都是老朋友了。
曾:我們這支紀錄片會對兩個書店的對照,你可以說一下你跟張老闆怎麼認識的?
陳:認識馬來西亞張老闆應該是他有次來台灣,因為圈子也蠻窄,我跟他味道也有點像,他有次來台灣有朋友就介紹來唐山,就認識一下。他出的主要是英文書為主吧,也是社會學這方面的。後來有一年我去回訪,剛好去吉隆坡有跟他見面,但是說真的英文書在台灣不是那麼好賣,而且隔了一個南洋也不方便,我也沒再去東南亞,所以跟張老闆大概五六年前見了面之後,到現在沒有再見過。而書的方面我也沒有跟他進書,因為從那邊運過來就是很大的問題,運費什麼的。
曾:你對他認識的程度是,譬如說你知道他以前被關過?
陳:那我大概知道一些,是別的朋友告訴我的。
曾:你有沒有想要跟他說的話?
陳:我現在腳把我困住了,我本來是想說我現在半退休狀態,多爭取時間去做田野調查,那是我年輕時的期望跟夢想,後來因為做生意就沒有時間去做田野,我田野的目標就是東南亞。主要就是人類學上東南亞跟我們關係最密切,南島民族嘛,不管馬來語或印尼語甚至是菲律賓的tagalo語,都是很接近阿美語,當然我們可以想像阿美族捕魚就散布出去了,所以我很想做這樣的調查。所以假如我腳方便了,我也想再去找張老闆。
曾:你開書店的時候,都聽什麼樣的音樂,店裡會放什麼音樂?
陳:以前放音樂沒問題,現在放音樂有版權、公播的問題,現在就放一些沒有版權問題的音樂。我當年喜歡的音樂,基本上是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高中的時候當然是聽搖滾樂,譬如說披頭四,高中時報紙批評披頭四是糜糜之音,我堂姊買了披頭四的黑膠唱片,我一聽覺得好好聽啊,哪裡是糜糜之音,就喜歡上聽西洋的流行音樂,美國的排行榜啊,或是中廣陶曉清的節目。後來上大學課業忙事情也多,發現我跟不太上了,有次聽了個學校的演講,是講電影音樂,我就開始對電影音樂很有興趣,後來比較聽古典音樂,也常聽百老匯的音樂劇,就比較沒有聽搖滾。
曾:那民歌時期你沒有加入?
陳:其實我是比較本土,我覺得民歌跟大陸的連結太強了,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我聽俄羅斯的國民樂派,那也是很有民族風的音樂,我覺得那比校園民歌好聽幾百倍,拉赫曼尼洛夫啊,多好聽。楊祖珺以前常在我這邊買書,不過很久沒看到她了,她本來還是林正杰的老婆時候就認識啦,我那時候也沒有概念說要辦什麼簽唱會,搞不好辦了滿滿的人。
曾:唐山都沒有賣過錄影帶嗎?以前還可以盜版的時候。
陳:沒有,因為我們空間有限,剛開店沒有那麼大,光賣書都沒地方放了。後來風潮一些原住民的唱片我有賣。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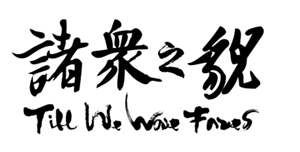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Leave a Comment